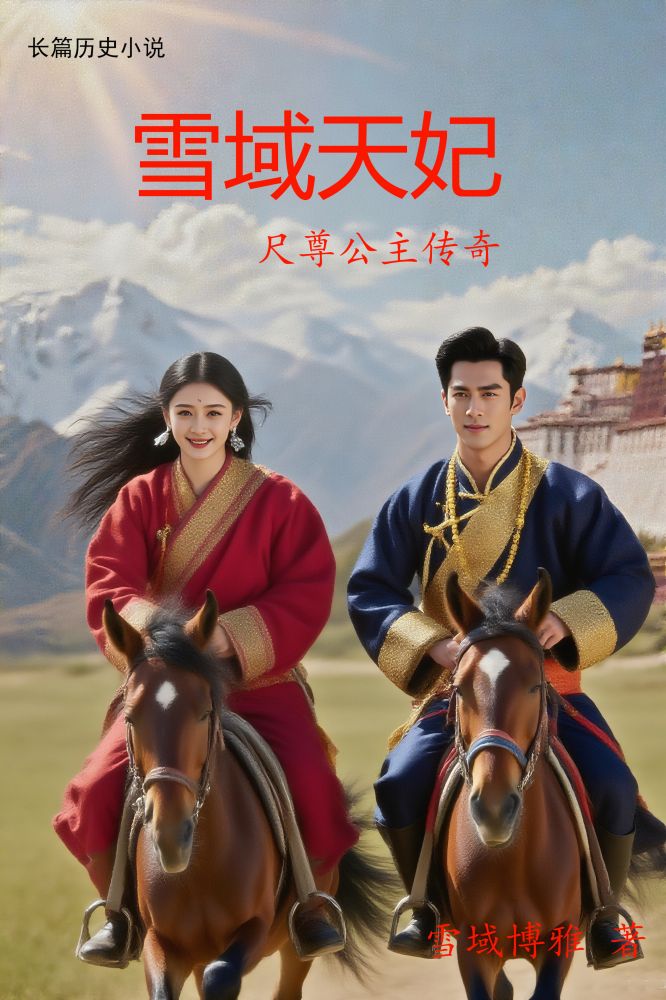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
第五卷 雪域梵音与文明交融
第二章 木石之争与雪山薪火
红山脚下的寺庙工地,在春末的暖阳里愈发热闹。自打地基用酥油、青稞粉与石灰混合的“雪域灰浆”筑牢后,下一步便是竖起大殿的立柱——按照王匠师带来的大唐营造法式,大殿需立十二根主柱,每根柱高逾三丈,直径需两人合抱,既要承托屋顶的重量,又要抵御雪域冬季的狂风。可当吐蕃工匠们将第一批砍伐的松木运到工地时,一场关于“木石”的争议,却突然在工匠群中爆发。
第一节 松木之辩:冻土上的材质之争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越过红山的峰顶,洒在工地中央的石料堆上,达瓦便带着十几个吐蕃工匠,推着木轮车往工地赶。车斗里装着刚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砍伐的松木,树皮还带着新鲜的树脂,散发着淡淡的松香气。“这些松木都是长了三十年的老料,质地紧实,去年我帮山南贵族建庄园时用过,抗风得很!”达瓦拍着一根松木的截面,纹理清晰可见,他脸上满是得意——为了找这些木料,他带着工匠在山里扎了三天帐篷,避开了雪崩多发区,才选到这批“最好的料子”。
可刚把木车停稳,王匠师就皱着眉走了过来。他蹲下身,用手指敲了敲松木的表面,又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把小凿子,轻轻凿下一小块木屑,放在手里捻了捻。“达瓦大叔,这松木不行。”王匠师的声音不高,却让周围的吐蕃工匠都安静了下来,“您看这木屑,质地太松软,而且松木里的树脂多,到了冬天冻土收缩,木材容易开裂;夏天拉萨河涨水,空气潮湿,还容易招虫蛀。”
达瓦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他站起身,比王匠师高出小半个头,双手叉在腰间:“王匠师,您是大唐来的,可能不知道我们雪域的情况。这念青唐古拉的松木,耐冻得很!去年冬天那么冷,山里的松树也没冻裂过,怎么到您这儿就不行了?”
“山里的松树长在土里,有根系固定,还能吸收水分调节湿度,可砍下来做立柱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”王匠师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卷图纸,摊开在石台上——那是大唐长安慈恩寺的立柱结构图,上面用墨线画着柱础、防潮层和木材处理的步骤,“您看,我们大唐建佛殿,用的都是楠木或柏木,这些硬木密度高,不易变形。而且木材砍伐后,要先在通风的地方阴干三年,去掉水分,再用桐油浸泡,这样才能防潮防蛀。”
“阴干三年?”一个年轻的吐蕃工匠忍不住喊了出来,“我们建寺庙哪有那么多时间?公主说今年冬天前要把大殿的框架立起来,等三年,雪都下好几场了!”
周围的吐蕃工匠纷纷附和:“就是,我们吐蕃的房子都是砍了木头就用,也没见哪栋塌了!”“大唐的法子太麻烦,不适合我们这儿!”议论声越来越大,甚至有几个工匠放下了手里的工具,盯着王匠师,眼神里带着不服气。
达瓦看着喧闹的工匠,又看了看王匠师紧绷的脸,心里也有些犯嘀咕。他知道王匠师是好意,可大唐的法子确实太“费时间”——松赞干布和尺尊公主都盼着寺庙早日建成,要是因为木材的事耽误了工期,谁也担不起责任。他正想开口劝说,却听到人群外传来一阵轻柔的脚步声,抬头一看,是尺尊公主和巴姆走了过来。
尺尊公主刚到工地,就察觉到了气氛不对。她走到石台前,拿起王匠师手里的木屑,又摸了摸那根松木的表面,转头问达瓦:“达瓦大叔,这些松木是从哪里砍的?砍伐后有没有处理过?”
“回公主,是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的林子里砍的,砍下来后就直接运过来了,没来得及处理。”达瓦如实回答,语气里带着一丝委屈,“我们想着早点把柱子立起来,不耽误工期。”
尺尊公主点了点头,没有立刻说话,而是转身对身后的巴姆说:“你去把去年山南贵族庄园的管家请来,就说我有事情问他。”巴姆应声跑开后,她才对工匠们说:“大家先别急,我们先看看实际情况再说。达瓦大叔说去年用松木建了庄园,那我们就去看看,那庄园的立柱现在怎么样了。”
半个时辰后,巴姆带着庄园管家回到了工地。那管家是个五十多岁的吐蕃人,脸上满是风霜,一见到尺尊公主就躬身行礼:“不知公主殿下找小的来,有什么吩咐?”
“去年达瓦大叔帮你们建的庄园,立柱用的也是这种松木,现在柱子有没有开裂或变形?”尺尊公主问道。
管家愣了一下,随即面露难色:“回公主,上个月庄园的西厢房柱子,确实裂了一道缝,大概有手指宽,我们还找了工匠用泥巴糊上,可这几天又裂开了。”
这话一出,周围的吐蕃工匠都安静了。达瓦的脸也红了,他没想到自己去年建的庄园,柱子真的出了问题。王匠师叹了口气,对达瓦说:“达瓦大叔,不是我故意挑毛病,而是这松木确实不适合做长期承重的立柱。您看,大唐的佛殿能存几百年,靠的就是选料和处理工艺,我们建的是要传给后世的寺庙,不能只图快,不图稳。”
达瓦低下头,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抬起头,语气里带着歉意:“王匠师,是我固执了。您说的对,寺庙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,不能马虎。那您说,我们该用什么木材?要是真要等三年,工期怎么办?”
王匠师见达瓦松了口,脸色也缓和下来。他指着图纸上的柱础部分:“其实不用等三年,我们可以用‘熏烤法’处理木材——把松木放在密闭的窑里,用松针和柏枝慢慢熏烤,去掉水分,再涂上酥油和桐油的混合物,这样处理下来,两个月就能用,虽然不如阴干三年的好,但在雪域也够用了。至于木材,我听说雅鲁藏布江北岸有一片柏树林,柏木比松木硬,还能防蛀,就是要穿过雪山去砍伐,路不好走。”
“雅鲁藏布江的柏木!”达瓦眼睛一亮,“我年轻时去过那里,那些柏木确实结实,而且有股特殊的香味,虫子不敢靠近。只是去那里要翻过米拉山口,现在这个季节,山口可能还有积雪,不好走。”
尺尊公主看着两人从争执到和解,心里也松了口气。她接过话头:“路不好走,我们就想办法克服。达瓦大叔,你熟悉山林,就负责带工匠去砍伐柏木;王匠师,你留在工地,指导大家搭建熏烤窑,处理已经运来的松木——这些松木虽然不能做主柱,却可以做横梁和门窗。”她顿了顿,又对周围的工匠们说:“大唐的技艺有大唐的优势,吐蕃的经验有吐蕃的用处,我们不是要争谁对谁错,而是要把好的法子结合起来,建一座最结实、最适合雪域的寺庙。”
工匠们纷纷点头,刚才的不满和抵触早已烟消云散。达瓦拍了拍王匠师的肩膀,笑着说:“王匠师,等我把柏木运回来,咱们再一起琢磨柱础的做法,你教我们大唐的防潮法子,我教你怎么在冻土上固定石柱,怎么样?”
“好!一言为定!”王匠师也笑了,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精致的木尺,递给达瓦,“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,丈量木料最准,你带着去,砍木的时候用得上。”
达瓦接过木尺,小心地揣进怀里,像是捧着一件珍宝。阳光洒在两人的脸上,之前的隔阂早已被“共同建寺”的目标取代——在雪域的工地上,不同的技艺,正从“对立”走向“相融”。
第二节 米拉山口:雪地里的互助之暖
三天后,达瓦带着二十个吐蕃工匠,推着十辆木轮车,往雅鲁藏布江北岸出发。随行的还有两个大唐工匠——王匠师特意派来的徒弟,一个叫李二,擅长辨认木材的质地;另一个叫赵三,会修理工具,还懂一些简单的吐蕃语。
“达瓦大叔,咱们这一路要走多少天?”李二坐在木轮车的边缘,手里拿着一个水囊,小口喝着酥油茶。他是第一次来雪域,看着路边连绵的雪山,眼睛里满是好奇,可走了半天,脚就开始疼——他穿的是大唐的布鞋,不如吐蕃工匠的皮靴耐走。
达瓦看了看天色,太阳刚升到半空,他指着远处的一个山坳:“今天我们先走到那曲的牧民帐篷,晚上在那里借宿,明天翻过米拉山口,后天就能到柏树林了。”他注意到李二揉着脚踝,便停下脚步,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双牦牛皮靴,递给李二:“这是我儿子阿古拉的靴子,他去年在雪灾里救人,腿被砸伤了,现在穿不了这么厚的靴子,你拿去穿,比你的布鞋暖和,也耐磨。”
李二愣了一下,看着那双靴子——靴面上缝着简单的云纹,是吐蕃工匠手工缝制的,靴底还钉着铁钉,能防滑。“达瓦大叔,这……这怎么好意思?”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?咱们都是为了建寺庙,你帮我们选木材,我给你双靴子,应该的。”达瓦拍了拍李二的肩膀,语气很诚恳。李二看着达瓦眼角的皱纹,想起自己在家乡的父亲——也是个木匠,总是把最好的工具留给徒弟,他心里一暖,接过靴子,小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赵三在一旁笑着说:“达瓦大叔,您这靴子做得比我们大唐的皮靴还结实,回头您教教我,我也给我爹做一双。”
达瓦被逗笑了:“行啊,等咱们把柏木运回去,我教你缝靴子,你教我修工具,咱们互相学!”
一行人说说笑笑地往前走,中午时分,终于到了那曲的牧民帐篷区。帐篷是黑色的牦牛毛织成的,一排排搭在草地上,远处的牧场上,牦牛群正低头啃着青草,一个穿着红色藏袍的小姑娘,正拿着鞭子追赶一只跑散的小羊。
“卓玛!”达瓦朝着小姑娘喊了一声。小姑娘抬起头,看到达瓦,眼睛一亮,蹦蹦跳跳地跑过来:“达瓦爷爷!您怎么来了?”
“我们要去雅鲁藏布江砍柏木,建寺庙用,路过这里,想在你们帐篷借宿一晚。”达瓦摸了摸卓玛的头,笑着说。卓玛的父亲是达瓦的远房亲戚,去年雪灾时,达瓦还帮他们家修过帐篷。
卓玛的父亲扎西听到声音,从帐篷里走出来。他穿着羊皮袄,手里拿着一个铜壶,看到达瓦一行人,立刻热情地招呼:“快进帐篷坐!我刚煮了酥油茶,还烤了青稞饼,你们路上累了,先喝点热的。”
走进帐篷,里面很宽敞,中间放着一个火塘,火塘里的牛粪火正旺,上面架着一个铜锅,酥油茶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卓玛忙着给大家倒茶,扎西则拿出青稞饼,放在石板上烤着,饼香混着酥油茶的香气,让一行人顿时忘了旅途的疲惫。
“达瓦爷爷,寺庙什么时候能建好啊?”卓玛坐在达瓦身边,托着下巴问,“上次文成公主来我们这里,给我娘治好了咳嗽,她说寺庙建好后,会有医师在里面给百姓看病,是真的吗?”
“是真的。”达瓦点点头,眼神里满是憧憬,“等寺庙建好了,不仅有医师看病,还有僧人讲经,大唐的工匠还会教我们种蔬菜,以后咱们雪域的百姓,日子会越来越好。”
扎西叹了口气:“说起来,去年雪灾的时候,要是有医师在,我邻居家的阿爸就不会走了。他就是得了风寒,没钱请法师,最后……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,卓玛也低下头,眼圈红红的。
李二听着,心里有些难受。他想起大唐的乡村里,每个村子都有药铺,百姓生病都能找医师看。“扎西大哥,等寺庙的医馆建好,我让文成公主派几个大唐医师过来,教你们认识草药,以后大家生病,就不用再担心了。”
扎西抬起头,眼里满是感激:“真的吗?那太好了!要是能学会认草药,我们牧民在山里放牧,也不怕生病没人治了。”
晚上,扎西杀了一只羊,烤了羊肉,还拿出自家酿的青稞酒,招待达瓦一行人。帐篷里,大家围着火塘,喝着青稞酒,唱着歌。达瓦弹着六弦琴,唱着吐蕃的牧歌,李二和赵三也跟着哼起了大唐的小调,卓玛则跳着锅庄舞,帐篷里的笑声和歌声,盖过了外面的风声。
第二天一早,天还没亮,扎西就起来给大家准备干粮——炒熟的青稞、风干的羊肉,还有灌满酥油茶的羊皮囊。“米拉山口这几天可能有小雪,你们路上要小心,要是遇到雪崩,就往山坳里躲。”扎西递给达瓦一张羊皮地图,上面用炭笔标出了山口的安全路线,“这是我去年赶牦牛时画的,沿着这条线走,能避开危险区。”
达瓦接过地图,紧紧握在手里:“扎西,谢谢你,等我们回来,一定给你带最好的柏木,帮你修个新帐篷。”
告别了扎西一家,一行人朝着米拉山口出发。刚走到山口脚下,天就开始飘起了小雪,雪花落在地上,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。达瓦让大家把木轮车的轮子用绳子绑上防滑布,又让每个人都系上绳索,连成一串——这样万一有人滑倒,其他人能拉一把。
“大家跟紧我,踩着我的脚印走!”达瓦走在最前面,他的皮靴踩在雪地上,留下深深的脚印。李二和赵三跟在中间,手里拿着木棍,探着前面的路。雪越下越大,风也越来越猛,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, visibility 越来越低,只能看到前面人的背影。
突然,走在最后的一个吐蕃工匠“啊”了一声,脚下一滑,连人带车摔在了雪坡上,木轮车顺着山坡往下滑,眼看就要撞到一块巨石。“不好!”达瓦回头一看,立刻解开腰间的绳索,朝着那个工匠冲过去。李二和赵三也反应过来,跟着冲上去,三个人一起拉住绳索,把工匠和木轮车往回拉。
可就在这时,山坡上方突然传来“轰隆”一声——雪崩了!大量的积雪从山顶滑下来,像一条白色的巨龙,朝着他们扑过来。“快往山坳里躲!”达瓦大喊一声,推着工匠往旁边的山坳跑。李二和赵三也赶紧拉着木轮车,跟着往山坳里躲。
积雪呼啸着从他们身边滑过,卷起的雪沫子把大家都埋了半截。等雪崩停下来,每个人身上都盖着厚厚的雪,像一个个雪人。达瓦咳嗽着,从雪堆里爬出来,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人数:“都没事吧?有没有人受伤?”
“我没事!”“我也没事!”工匠们纷纷从雪堆里爬出来,只有李二抱着腿,脸色发白。达瓦赶紧走过去,掀开李二的裤腿——膝盖被石头磕破了,流了不少血。“别动,我这里有草药。”达瓦从布包里拿出一株晒干的“雪莲花”,这是他在山里采的,能止血消炎。他把雪莲花嚼碎,敷在李二的伤口上,又用布条缠好。
“达瓦大叔,对不起,都怪我,差点让大家遇险。”李二低着头,声音里带着愧疚。
“不怪你,是雪崩来得太突然了。”达瓦拍了拍李二的肩膀,“咱们能平安躲过,就是好事。你先在山坳里休息一会儿,我们把木轮车整理好,等雪小了再走。”
赵三蹲在一旁,检查着木轮车的轮子,发现有一个轮子被撞坏了。他从工具箱里拿出锤子和钉子,开始修理轮子,嘴里还哼着大唐的小调。达瓦看着他,又看了看躺在雪地上休息的李二,心里突然觉得很温暖——这些大唐来的工匠,虽然和他们语言不同,生活习惯也不一样,可在危险面前,却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,这种“不分你我”的情谊,比什么都珍贵。
雪渐渐小了,阳光透过云层,洒在雪地上,泛着耀眼的光。达瓦扶着李二站起来,赵三也修好了木轮车。一行人重新系上绳索,朝着山口的另一边走去。雪地上,他们的脚印连成一串,像一条长长的线,连接着雪山和远方的柏树林——那不仅是木材的目的地,更是不同文明在雪域土地上,用“互助”编织的纽带。
第三节 壁画之融:梵彩与藏色的碰撞
就在达瓦一行人在雪山中寻找柏木时,寺庙工地的佛塔壁画绘制,也正式提上了日程。按照鸠摩罗什的提议,佛塔的内壁要绘制“佛陀一生”的故事,从诞生、出家、修行到涅槃,共分为八幅壁画,每一幅都要体现出“三国交融”的特色——既有天竺的梵式画风,又有大唐的工笔技法,还要融入吐蕃的色彩审美。
负责绘制壁画的,是天竺来的画僧智藏和吐蕃最有名的画师洛桑。智藏是鸠摩罗什的弟子,在天竺时就以绘制佛画闻名,他带来的颜料都是从天竺经丝绸之路运来的,有从矿物中提取的群青、赭石,还有从植物中榨取的藤黄、胭脂,色彩鲜艳,不易褪色。洛桑则是吐蕃本土的画师,擅长用天然的矿物和植物制作颜料,比如用绿松石磨成的绿色,用珊瑚磨成的红色,还有用狼毒花制作的白色,他绘制的壁画,充满了雪域的粗犷与灵动。
可当两人第一次在佛塔的内壁前碰面时,就因为“画风”的问题,产生了分歧。
“洛桑画师,佛陀诞生图应该按照天竺的范式来画——佛陀出生时,天降甘霖,九龙吐水为他沐浴,背景要用群青绘制蓝天,象征佛法的浩瀚。”智藏拿着炭笔,在墙上勾勒出大致的轮廓,线条细腻,比例精准,完全遵循天竺佛画的传统。
洛桑站在一旁,皱着眉摇了摇头。他拿起自己的画笔,在智藏的轮廓旁边,画了一座雪山:“智藏大师,这里是雪域,不是天竺。佛陀诞生图里,应该有雪山和牦牛,这样吐蕃的百姓才能看懂,才能感受到佛陀就在我们身边。而且您用的群青,颜色太鲜艳,我们吐蕃的百姓更喜欢柔和的绿色和蓝色,就像拉萨河的水和远处的雪山。”
智藏放下炭笔,脸色有些严肃:“洛桑画师,佛画是庄严的,不能随意更改范式。天竺的佛陀诞生图,传承了几百年,每一笔都有深意,怎么能随便加雪山和牦牛?这是对佛陀的不敬。”
“我没有不敬!”洛桑也有些激动,“我们吐蕃的画师,绘制山神和河神的画像时,都会加入雪山、草原的元素,这样百姓才会觉得亲切,才会信仰。佛陀的画像也是一样,要是画得和天竺一模一样,百姓看不懂,怎么会相信佛法能守护他们?”
两人各执一词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周围的小画师们都不敢说话,只能看着他们,场面一度很尴尬。鸠摩罗什听到争吵声,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他看了看墙上的两幅草图,又看了看智藏和洛桑紧绷的脸,笑着说:“你们俩都别争了,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”
智藏和洛桑都安静下来,看着鸠摩罗什。
“我年轻时在天竺游学,遇到过一位老画僧。有一次,他要在一座偏远的山村绘制佛画,村民们都是农民,不懂天竺的佛画范式。老画僧没有按照传统来画,而是在佛陀的身边,画了农民们耕种的田地、收割的麦子,还有他们养的牛羊。村民们看到壁画后,都很感动,说‘原来佛陀也和我们一样,关心我们的生活’,从此都虔诚地信仰佛法。”鸠摩罗什顿了顿,又说:“佛法讲究‘因地制宜’,佛画也是一样。天竺的范式有天竺的智慧,吐蕃的特色有吐蕃的心意,为什么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呢?”
智藏低下头,若有所思。他想起自己在天竺时,也曾为了让不同地区的百姓理解佛法,调整过画中的细节。洛桑也有些不好意思,他刚才确实太激动了,没有考虑到佛画的庄严性。
这时,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也走了进来。文成公主看着墙上的草图,笑着说:“智藏大师的线条细腻,色彩鲜艳,很有天竺的韵味;洛桑画师的雪山和牦牛,充满了吐蕃的特色,要是能把两者结合,一定是一幅最好的壁画。”她指着智藏画的“九龙吐水”,又说:“你们看,这九龙吐水,可以把水画成拉萨河的样子,蜿蜒流淌,旁边加上雪山;背景的蓝天,可以用智藏大师的群青,再加入洛桑画师的绿松石绿,这样既有天竺的庄严,又有吐蕃的灵动。”
尺尊公主也补充道:“还有佛陀的服饰,天竺的佛衣多是轻薄的纱质,我们可以在上面绣上吐蕃的卷草纹,再用大唐的工笔技法勾勒边缘,这样三国的特色就都体现出来了。百姓看到这样的壁画,既能感受到佛法的庄严,又能看到自己熟悉的事物,自然会喜欢。”
智藏和洛桑对视一眼,都露出了笑容。智藏拿起炭笔,在“九龙吐水”的旁边,画了一座小小的雪山;洛桑则在佛陀的衣袍上,添上了吐蕃特色的卷草纹。两人一个勾勒线条,一个调配色彩,配合得越来越默契。
接下来的几天,佛塔内壁的绘制渐渐步入正轨。智藏教吐蕃的小画师们天竺的透视技法,让壁画更有立体感;洛桑则教智藏如何用雪域的天然颜料制作色彩,比如用狼毒花制作的白色,涂在墙上不仅不易褪色,还能防虫蛀。
有一次,智藏在绘制“佛陀修行图”时,遇到了难题——他想画一棵菩提树,可按照天竺的画法,菩提树的叶子是椭圆形的,可吐蕃的百姓只见过松树和柏树,不知道菩提树是什么样子。洛桑看到后,提议道:“智藏大师,我们可以把菩提树的叶子画成松树叶子的形状,但保留菩提树的枝干,这样百姓一看就知道是‘神圣的树’,又不会觉得陌生。”
智藏采纳了洛桑的建议,还在菩提树的旁边,画了一个吐蕃的转经筒。“这样一来,佛陀修行时,就像在我们雪域的草原上一样。”智藏笑着说,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种“交融”的画法,每一笔都充满了新意。
洛桑也从智藏那里学到了很多。有一次,他在调配红色颜料时,总是觉得颜色不够鲜亮。智藏告诉他,在珊瑚粉里加入一点天竺带来的胭脂,颜色会更鲜艳,还能防水。洛桑按照智藏的方法试了试,果然,红色变得明亮又柔和,涂在墙上,像雪域的晚霞一样美丽。
这天傍晚,尺尊公主来看壁画的进展。佛塔的内壁上,已经完成了四幅壁画:佛陀诞生图里,九龙吐水落在拉萨河中,旁边的雪山上,牦牛在悠闲地吃草;佛陀出家图里,佛陀穿着绣有吐蕃卷草纹的袈裟,背景是大唐风格的亭台楼阁,远处是天竺的寺庙轮廓。每一幅壁画,都融合了三国的特色,色彩斑斓,却又和谐统一。
“太好了!”尺尊公主看着壁画,脸上满是欣慰,“智藏大师,洛桑画师,你们用画笔把三国的友谊和文化都画在了墙上,这座佛塔,不仅是佛法的象征,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。”
智藏和洛桑都躬身行礼。智藏笑着说:“这都是公主殿下和文成公主的指点,还有洛桑画师的帮助。我现在明白,佛画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要随着地域和文化的不同,不断创新,这样才能让佛法真正融入百姓的生活。”
洛桑也说:“以前我觉得,吐蕃的画法是最好的,现在才知道,大唐的工笔和天竺的范式,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以后我要多向智藏大师请教,把更多的好技法带回吐蕃。”
夕阳的余晖透过佛塔的窗户,洒在壁画上,色彩显得更加鲜艳。智藏和洛桑并肩站在壁画前,讨论着下一幅“佛陀涅槃图”的细节,他们的声音很轻,却充满了默契——在这座正在建设的佛塔里,梵彩与藏色的碰撞,最终化作了“交融”的温暖,像雪域的阳光一样,照亮了每一面墙壁。
第四节 医馆初立:苯教与大唐的和解
随着佛塔壁画的绘制和立柱材料的筹备,寺庙附属的医馆也开始动工。按照尺尊公主的设想,这座医馆要分为“诊疗区”和“草药区”——诊疗区由大唐医师、天竺僧医和吐蕃苯教法师共同坐诊,草药区则种植大唐带来的草药种子和吐蕃本土的草药,让不同的医疗理念在这里交流、融合。
负责医馆筹备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大唐医师孙思邈(注:此处为虚构设定,与历史人物同名,非真实历史事件)和吐蕃苯教法师贡布。孙思邈擅长望闻问切,带来了大唐的《黄帝内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,还带了不少草药种子,比如当归、黄芪、甘草,这些草药在大唐常用于治疗风寒、脾胃虚弱等病症。贡布则是吐蕃最有名的苯教法师,擅长用吐蕃本土的草药和祈福仪式治疗疾病,比如用雪莲花治疗风湿,用经幡祈福驱散“邪气”,他在吐蕃百姓中威望很高,很多牧民生病都会找他。
可当孙思邈和贡布第一次在医馆的选址前碰面时,就因为“治疗理念”的不同,产生了矛盾。
那天上午,孙思邈正在指挥工匠搭建草药棚,他带来的大唐药童们,正忙着把草药种子分类,准备播种。贡布带着几个苯教弟子,拿着经幡和法器,走到医馆的地基前,开始念诵苯教的祈福经文,还在地基的四个角上,插上了带有苯教符号的木牌。
“贡布法师,您这是在做什么?”孙思邈皱着眉走过去,他不理解为什么建医馆还要搞“祈福仪式”,“医馆是治病救人的地方,靠的是草药和医术,不是祈福和咒语。您这样做,会让百姓觉得治病要靠‘邪气’,而不是靠医师。”
贡布停下诵经,抬起头,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满:“孙医师,您是大唐来的,可能不懂我们吐蕃的规矩。建医馆要先祭拜土地神和山神,祈求他们保佑医馆平安,这样草药才能长得好,病人才能治好。您只相信草药,不相信神灵,是对我们吐蕃信仰的不尊重。”
“我不是不尊重你们的信仰,而是觉得治病要讲‘实效’。”孙思邈从药箱里拿出一株晒干的黄芪,递给贡布,“这是大唐的黄芪,能补气养血,治疗疲劳乏力,很多百姓吃了都有效。可您的祈福仪式,能让病人的身体变好吗?能让草药长高吗?”
“祈福仪式能驱散病人身上的‘邪气’,这比草药更重要!”贡布有些激动,他举起手中的法器,“去年山南有个牧民得了重病,找了很多医师都治不好,最后是我给他祈福,又用雪莲花给他泡澡,他才好起来的。这就是神灵的力量!”
“那是因为雪莲花有消炎止痛的功效,不是因为祈福!”孙思邈也提高了声音,“您要是只给病人祈福,不给他们用草药,他们的病能好吗?”
两人吵得越来越凶,周围的工匠和药童都围了过来,议论纷纷。有的吐蕃工匠支持贡布,觉得建医馆确实要祭拜神灵;有的大唐药童则支持孙思邈,觉得祈福没用,还是医术重要。
就在这时,巴姆带着一个牧民匆匆跑了过来。那牧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,孩子脸色苍白,嘴唇发紫,呼吸急促,看起来病得很重。“孙医师!贡布法师!快救救这个孩子!他昨天在雪地里玩,受了风寒,现在一直发烧,还咳嗽,喝了草药也没用!”巴姆的声音里满是焦急。
贡布立刻走过去,摸了摸孩子的额头,又看了看孩子的舌苔,脸色凝重:“这孩子是被‘寒邪’入侵了,得赶紧祈福,驱散邪气!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铜铃,开始在孩子身边摇晃,嘴里念着苯教的经文,还让弟子拿来一碗清水,对着清水念咒,然后要给孩子喝。
孙思邈拦住了他:“贡布法师,这孩子是风寒入肺,引发了肺炎,再耽误下去会有危险!得先给他退烧,再用草药消炎!”他让药童拿来银针和退烧药,准备给孩子针灸退烧。
“你别碰他!要是你的银针伤了孩子,怎么办?”贡布挡住孙思邈,不让他靠近孩子。
“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!再耽误,孩子就没命了!”孙思邈急得满头大汗,他看着孩子越来越微弱的呼吸,心里像火烧一样。
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,尺尊公主赶了过来。她看到孩子的情况,立刻对两人说:“别争了!贡布法师,您先给孩子祈福,稳定他的情绪;孙医师,您赶紧准备针灸和草药,咱们一起救孩子!”
贡布和孙思邈对视一眼,都点了点头。贡布继续念诵经文,摇晃着铜铃,孩子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,不再哭闹。孙思邈则快速拿出银针,在孩子的太阳穴、合谷穴等穴位上轻轻刺入,又让药童煮了一碗退烧药,里面加了少量的甘草,用来调和药性。
半个时辰后,孩子的体温渐渐降了下来,呼吸也变得平稳了。贡布停止了祈福,看着孩子好转的脸色,心里有些惊讶——他没想到大唐的针灸和草药,效果这么快。孙思邈也松了口气,他看着贡布,语气缓和了不少:“贡布法师,您的祈福仪式,能让孩子平静下来,这对治疗也有帮助。”
贡布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:“孙医师,您的针灸和草药,确实很厉害。以前我觉得祈福最重要,现在才知道,草药和医术也很重要。”
孩子的母亲跪在地上,对着尺尊公主、孙思邈和贡布连连磕头:“谢谢公主!谢谢医师!谢谢法师!是你们救了我的孩子!”
尺尊公主扶起她,笑着说:“不用谢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以后医馆建好了,孙医师会教大家认识草药,贡布法师也会继续为百姓祈福,咱们一起为吐蕃的百姓治病。”
从那以后,孙思邈和贡布的关系渐渐缓和了。孙思邈开始向贡布请教吐蕃本土草药的用法,比如雪莲花怎么用才能更好地治疗风湿,狼毒花怎么处理才能解毒。贡布也开始学习大唐的医术,他让孙思邈教他望闻问切,还让弟子们跟着大唐药童一起种植草药。
有一次,一个老年牧民得了严重的风湿,关节又肿又痛,走不了路。贡布先用苯教的祈福仪式,为老人驱散“寒邪”,然后孙思邈用大唐的针灸,刺激老人的穴位,缓解疼痛,最后两人一起,用雪莲花和当归煮了一碗药汤,让老人喝下去。几天后,老人的风湿就好了很多,还能拄着拐杖走路了。
“孙医师,原来草药和祈福结合起来,治病这么有效!”贡布看着好转的老人,脸上满是笑容。
孙思邈也笑着说:“是啊,大唐的医术有大唐的优势,吐蕃的祈福有吐蕃的心意,两者结合,才能更好地为百姓治病。以后咱们就在医馆里,一起为百姓服务。”
医馆的草药棚很快就搭建好了,里面种满了大唐的草药和吐蕃的本土草药。孙思邈和贡布一起,在草药棚前立了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“汉藏草药共植,医法相融济民”——这不仅是医馆的宗旨,更是不同医疗理念在雪域土地上“和解”的见证。
夕阳下,孙思邈和贡布并肩站在草药棚前,看着药童们忙碌的身影,听着远处工地上传来的工匠们的歌声,两人的脸上都满是欣慰。在这座正在建设的寺庙和医馆里,苯教的祈福与大唐的医术,正像雪域的阳光和雨露一样,共同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百姓,也滋养着不同文明交融的“薪火”。
而此时,达瓦一行人也终于翻越了米拉山口,找到了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柏树林。当第一根粗壮的柏木被砍伐下来,装上木轮车时,达瓦抬头望向远方的红山——他知道,那座承载着三国友谊和文明交融的寺庙,很快就要竖起第一根真正的“立柱”,而雪域的梵音,也将在不久的将来,响彻红山脚下,传遍整个雪域高原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