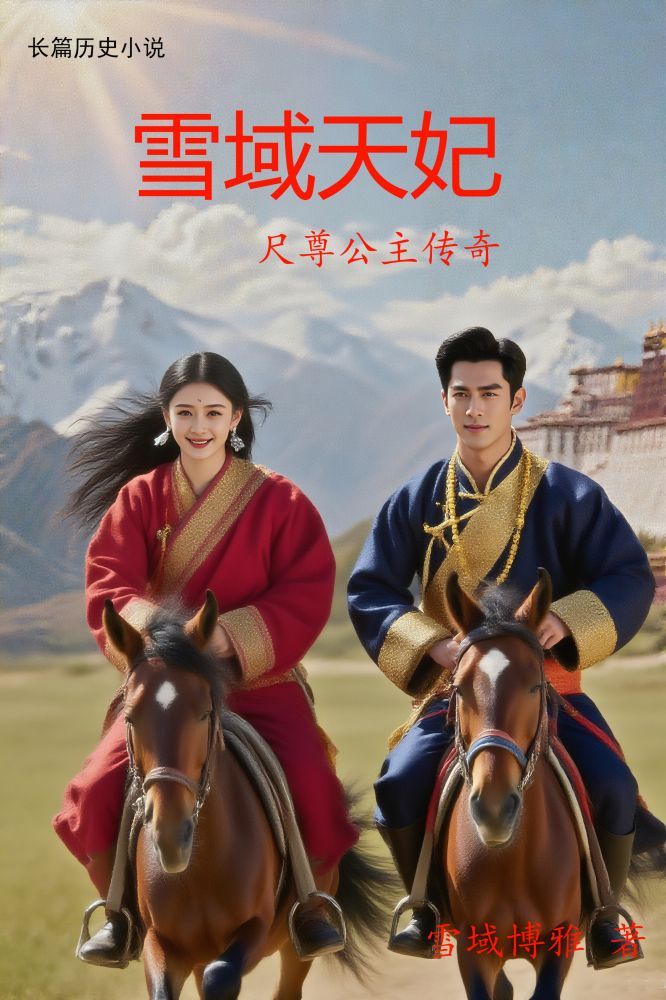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
第一卷:迦舍末罗的红
第五章 红山的风
逻些城的风,是带着砂砾的。
布里库提的马车碾过最后一道山梁时,红山宫殿的金顶突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,像块被太阳晒化的金子,淌在灰褐色的山岩上。护送的珞巴猎手发出一声欢呼,手里的长矛指向远处——城郭的轮廓在风里若隐若现,夯土的城墙被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壑,像位饱经风霜的老者,咧着缺牙的嘴在笑。
“那就是赞普的宫殿。”禄东赞的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,他勒住马,黑氆氇大袍被风掀起一角,露出腰间的蛇纹弯刀,“吐蕃的心脏,就跳在那座红山上。”
布里库提掀起车帘的手顿了顿。指尖沾着的雪粒已经化了,留下点冰凉的湿痕,像她此刻的心情。从加德满都出发的第三十二天,他们翻越了七座雪山,渡过五条冰河,终于抵达了这片既陌生又与她血脉相连的土地。远处的城郭里,隐约能听见苯教寺院的法号声,呜呜咽咽的,混着风里的砂砾,刮得人耳膜发疼。
“公主,您看那些经幡。”达拉的声音带着惊叹,她扒着车窗,绿裙的袖子被风卷得老高,“比迦舍末罗的佛堂经幡多好多!”
布里库提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——红山脚下的山坡上,插满了五彩的经幡,红、白、蓝、绿、黄,在风里猎猎作响,像无数只振翅的鸟。她认得那些布料上印着的经文,是藏文的六字真言,只是字体比母亲教她的更粗犷,带着股山石般的坚硬。
“吐蕃人相信,经幡动一次,就像把经文念了一遍。”禄东赞不知何时凑到了车窗边,刀疤在阳光下泛着暗红的光,“红山的风,一年到头都不停,这里的经文,也就永远念不完。”
马车驶进逻些城时,布里库提闻到了股混杂着酥油、牲畜粪便和尘土的味道。街道两旁的土房低矮而密集,房檐下挂着风干的牛羊肉,像一串串暗红色的钟乳石。穿藏袍的人们站在路边,好奇地打量着这支队伍,孩子们追着马车跑,手里举着刚从河里捞的冰碴,笑声脆得像碎玻璃。
“他们在看什么?”达拉有些不安地攥紧了布里库提的衣角,绿裙的料子被她捏出了褶皱。
“在看迦舍末罗的孔雀。”布里库提轻轻拍了拍她的手,指尖抚过发间的绿松石——那是珞巴首领送的碗底松石,被她穿成了发饰,“别怕,我们带着佛的祝福呢。”
她的目光落在人群里一位老阿妈身上。老人穿着件褪色的褐氆氇,手里转着个小小的经筒,看见马车时,突然举起经筒对着她们的方向拜了拜,嘴角的皱纹里沾着点酥油,像朵盛开的优昙婆罗。
红山宫殿的大门比想象中简陋,是用整根松木制成的,门板上钉着铜钉,拼成苯教的“永固”符号。守门的甲士穿着铁甲,甲片上的锈迹被风磨得发亮,看见禄东赞,突然单膝跪地,甲胄碰撞的声音在空荡的广场上格外刺耳。
“赞普在‘红宫’等您。”禄东赞扶着布里库提下车,他的手很稳,掌心的老茧蹭过她的手腕,像在传递某种力量,“记住,见到赞普时,不必行跪拜礼——您是迦舍末罗的公主,不是吐蕃的奴隶。”
布里库提的裙摆扫过宫殿前的石板地,上面刻着的莲花纹已经被无数双脚磨平了棱角。她忽然想起母亲梳妆台上的铜镜,也是这样,被岁月磨去了锋芒,却依旧能照见人心。
红宫的大殿比加德满都的孔雀殿更开阔,却少了几分精致。四壁的壁画是新绘的,颜料还带着股生涩的气味,画的是吐蕃勇士开疆拓土的场景,长矛上挑着敌人的头颅,血色红得像要滴下来。殿中央的宝座上铺着张完整的雪豹皮,毛色在酥油灯的光里泛着银白的光,像堆凝固的雪。
松赞干布就坐在那张宝座上。
他比布里库提想象中年轻,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,穿件赭红色的赞普袍,领口和袖口绣着金边的卷草纹,比禄东赞的氆氇更显华贵。他的眼睛很深,像藏北的湖泊,望过来时带着股穿透力,仿佛能看穿人心里的秘密。他没戴王冠,只是在发间系了根红绸带,末端缀着颗鸽卵大的红珊瑚,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。
“欢迎你,迦舍末罗的公主。”他的尼泊尔语很流利,甚至带着点加德满都的软调,不像禄东赞那样带着铁锈味,“旅途还顺利吗?”
布里库提弯腰行礼,指尖触到腰间的三世珠——蜜蜡的温度透过衣料传过来,让她想起父亲的叮嘱。“托赞普的福,一路平安。”她的目光落在他宝座旁的一个铜盆上,里面盛着清水,水面上漂着片绿绒蒿的叶子,像她埋在苯教祭坛的那一朵。
松赞干布笑了笑,那笑容冲淡了他眼底的锐利,多了几分温和。“禄东赞说,你在雪山里收服了珞巴人。”他的手指在宝座的扶手上轻轻敲击着,节奏像在转经筒,“用你母亲的降魔杵。”
布里库提的心猛地一跳。原来禄东赞早就把路上的事汇报了。她握紧了降魔杵的银链,杵头的莲花纹硌着掌心:“不是收服,是他们认出了母亲的信物。珞巴人是雪山的孩子,比谁都懂得感恩。”
“说得好。”松赞干布从宝座上站起来,雪豹皮被他的袍角掀起一角,露出底下刻着的九头蛇纹——和她母亲铜镜上的图案,竟有几分相似,“雪山的子民,最看重的就是‘信’字。”他走到她面前,身高比她高出一个头,身上的檀香混着皮革的味道,像雪山阳坡的风,“我听说,你带来了迦舍末罗的‘智慧’?”
布里库提知道他指的是盟书。她从锦囊里掏出那个缠着红绸的牛皮卷轴,没有立刻递过去,而是捧在手心:“盟书里写的,不只是疆土的约定,还有我母亲的心愿——她说,喜马拉雅山的南北,本就是同一片天,不该被战火隔开。”
松赞干布的目光落在卷轴上的九头蛇铜锁上,忽然伸手,指尖在锁身上轻轻碰了一下。“你母亲是位了不起的女性。”他的声音低沉了些,“当年若不是她带着盟书离开,吐蕃的内乱还要持续更久。”
布里库提的惊讶藏不住了:“赞普认识我母亲?”
“我见过她一次。”松赞干布转身走回宝座,红绸带末端的红珊瑚晃得人眼花,“在我十岁那年,她来逻些城朝拜,给我带了串蜜蜡珠,说能保平安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发间,红绸带下面,果然露出串蜜蜡珠的线头,和她的三世珠质地一模一样。
殿外的风突然大了,吹得窗棂上的经幡哗哗作响。布里库提忽然觉得,那些看似遥远的往事,其实一直像红山的风一样,在她不知道的地方流动着,将她和眼前的这个男人,和这片土地,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“盟书先由你收着。”松赞干布重新坐下,雪豹皮又恢复了原状,“等你在逻些城住惯了,再决定要不要打开它。”他拍了拍手,从殿后走出几位侍女,都穿着吐蕃的氆氇裙,为首的那位眉眼间带着股英气,发间别着支银制的狼头簪。
“这是梅朵,”松赞干布介绍道,“她是吐蕃大相的女儿,以后由她陪你熟悉这里的一切。”
梅朵走上前,弯腰行礼,动作标准却带着股疏离:“公主殿下,请到偏殿歇息吧。您的嫁妆已经安置好了,就在‘绿绒苑’——那里种满了从藏北移来的绿绒蒿,您应该会喜欢。”
她的声音很脆,像冰块碰撞,却少了几分暖意。布里库提注意到她的狼头簪尖上,刻着个小小的苯教符号,和她在祭坛上见过的“卍”字不一样,更像一把锋利的刀。
离开红宫时,布里库提回头望了一眼。松赞干布还坐在那张雪豹皮宝座上,手里转着个小小的经筒,侧脸在酥油灯的光里一半明一半暗,像幅没画完的壁画。她忽然觉得,这个年轻的赞普,比喜马拉雅山的风雪还要难懂——他的温和里藏着锐利,他的疏离里又带着某种熟悉感。
绿绒苑果然种满了绿绒蒿。紫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,像一片被打翻的颜料,和加德满都的优昙婆罗是截然不同的美。苑子里的房屋是新建的,用的是迦舍末罗的样式,屋顶却盖着吐蕃的牦毛毡,像两个王朝的拼接。
“公主,您看那尊度母像。”达拉指着院子中央的佛龛,眼睛亮了起来,“和我们佛堂的一模一样!”
布里库提走过去,发现那尊度母像果然是尼泊尔风格的,眉眼间带着悲悯,和母亲画像里的神情如出一辙。像前的香炉里插着三炷香,香灰还是热的,显然刚有人祭拜过。
“是赞普让人从加德满都请来的。”梅朵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她抱着件新的氆氇袍,站在绿绒蒿丛里,狼头簪在阳光下闪着冷光,“赞普说,要让公主在逻些城,也能闻到家乡的味道。”
她的语气听不出是真心还是嘲讽。布里库提接过氆氇袍,布料比她身上的更厚实,带着股淡淡的松烟味,像曲珍阿妈烧的香。
“替我谢谢赞普。”布里库提的指尖抚过氆氇上绣的绿绒蒿,针脚很密,像达拉在雪地上画的九头蛇,“也谢谢梅朵姑娘特意过来。”
梅朵没说话,只是转身离开了,狼头簪的影子投在地上,像只蓄势待发的小兽。布里库提看着她的背影,忽然想起禄东赞说的话:“吐蕃的宫廷,比雪山的暗流更复杂。每个笑脸背后,都可能藏着把刀。”
夜里,逻些城的风更急了,吹得绿绒苑的窗纸哗哗作响,像有人在外面拍门。布里库提坐在灯下,打开了母亲的梳妆盒——里面除了铜镜和降魔杵,还有一小包藏红花,是她从加德满都带来的,据说能安神。
她把藏红花撒进酥油茶里,看着红色的花丝在奶白色的茶里慢慢散开,像迦舍末罗的红,渗进了吐蕃的白。窗外的绿绒蒿在风里摇曳,影子投在墙上,像无数只跳动的火焰,映着她掌心的三世珠,发出温润的光。
她知道,从踏入红山宫殿的这一刻起,她的“传奇”才真正开始。不是在加德满都的佛堂里,也不是在雪山的旅途中,而是在这片风带着砂砾的土地上,在这座红与白交织的宫殿里,在佛与苯、迦舍末罗与吐蕃的碰撞里,用她的血脉,她的智慧,她的坚韧,去续写母亲未完成的故事。
红山的风还在吹,像在为她唱一首古老的歌谣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