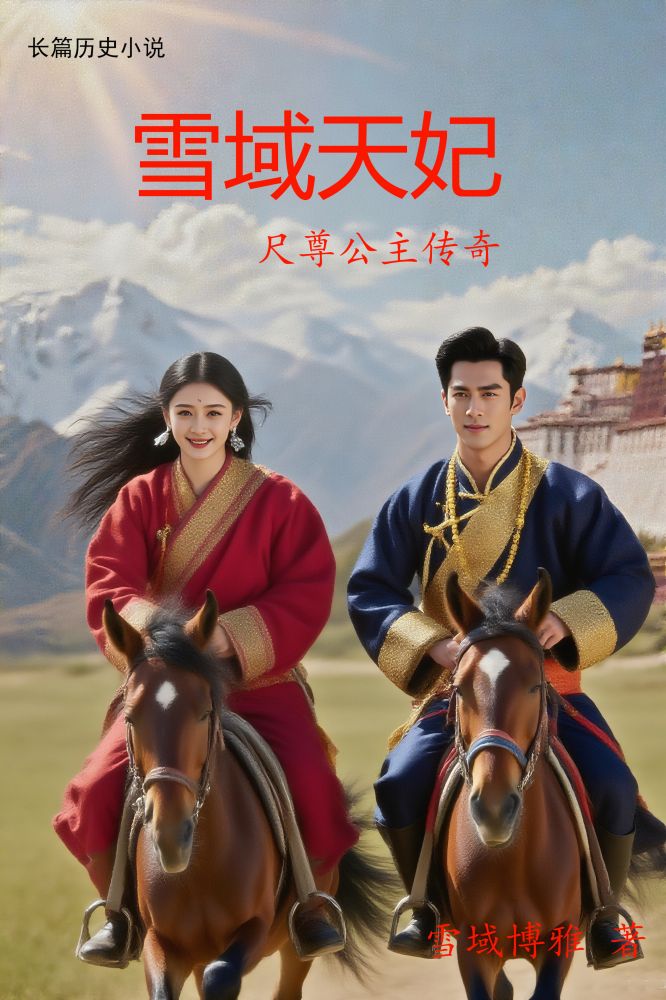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
第五卷 雪域梵音与文明交融
第三章 立柱盛典与烟火情长
红山脚下的寺庙工地,在初夏的风里迎来了最热闹的日子——大殿主柱的立起仪式,定在藏历五月十五这天。前一日,达瓦带着砍伐好的柏木,终于从雅鲁藏布江北岸归来,二十根粗壮的柏木被整齐地堆在工地中央,木材表面涂着酥油与桐油混合的涂层,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,连树皮的纹路里都浸透着淡淡的柏香。王匠师带着工匠们连夜打磨柱础,用“雪域灰浆”将青石板砌成的柱础固定在地基中,每一块石板的缝隙都填得严丝合缝,连指尖都插不进去。
第一节 晨露里的筹备:酥油香与铜铃声
藏历五月十五的清晨,天还没亮透,红山脚下就飘起了酥油茶的香气。工地东侧的空地上,十几个吐蕃妇女围坐在火塘边,正忙着准备庆典的食物。卓玛穿着一身新做的红色藏袍,藏袍的领口和袖口缝着银线绣的卷草纹,走动时,腰间的银饰叮当作响。她蹲在火塘前,手里拿着一个黄铜茶壶,正用力搅拌壶里的酥油茶——茶砖是去年储存的老茶,熬煮时加了牦牛奶和小块的酥油,搅拌时,茶沫子在壶里翻涌,像堆起的小雪山。
“卓玛,你这酥油茶打得不够浓,得再用点劲!”旁边的拉姆阿妈笑着说。拉姆阿妈是那曲的牧民,听说寺庙要立柱,特意带着自家的酥油和青稞粉赶来帮忙。她手里拿着一个石臼,正将青稞粒捣成粉,石臼碰撞的“咚咚”声,和卓玛搅拌茶的“哗啦”声混在一起,格外有生活气息。
卓玛吐了吐舌头,把茶壶抱得更紧,手臂上的肌肉微微绷紧,脸颊因为用力而泛起红晕:“阿妈,我知道啦!上次文成公主喝了我打的酥油茶,说有‘太阳的味道’,这次我要让大家都尝到!”说着,她掀开茶壶盖,用勺子舀起一勺茶,茶沫子挂在勺沿上,像一层厚厚的奶霜,她凑到鼻尖闻了闻,满足地笑了——这香气里,有酥油的醇厚,有茶叶的回甘,还有清晨露水的清润。
不远处,几个大唐工匠的妻子正学着做青稞饼。李二的妻子杏花穿着一身浅蓝色的唐装,手里捏着一团青稞面团,笨拙地模仿着吐蕃妇女的样子,将面团拍成圆形。她的手指沾了面粉,额头上也沾了一点,像个刚学手艺的孩子。吐蕃妇女卓嘎看着她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:“杏花姐,面团要先揉到光滑,再用手掌慢慢压,不然饼会裂的。”说着,卓嘎拿起一团面团,手指灵活地揉捏起来,面团在她手里像有了生命,转了几圈就变得光滑圆润,再往石板上一压,边缘整齐得像用尺子量过一样。
杏花跟着卓嘎的动作学,指尖渐渐有了感觉。她把压好的青稞饼放在火塘边的石板上,石板被牛粪火烤得发烫,饼刚放上去,就发出“滋滋”的轻响,青稞的香气立刻飘了出来。“真的不裂了!”杏花惊喜地说,她拿起自己烤好的第一块青稞饼,饼面上带着焦黄色的斑点,咬一口,外脆里软,还带着淡淡的甜香,“比我们大唐的麦饼还好吃!”
卓嘎笑着递过来一小碗奶渣:“蘸着奶渣吃更甜,这是我昨天用牦牛奶做的,你试试。”杏花接过奶渣,放在嘴里,奶渣的酸香和青稞饼的甜香混在一起,味蕾像是被唤醒了一样,她忍不住又咬了一大口,嘴角沾了奶渣也没察觉。
工地的另一侧,几个苯教弟子正忙着挂经幡。经幡是用五彩的棉布做的,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绿五种颜色,分别代表着太阳、大地、蓝天、白云和草原。他们踩着木梯,将经幡的一端系在工地周围的木桩上,另一端让风吹着,经幡在空中展开,像一群飞舞的彩蝶。贡布法师手里拿着一个铜铃,沿着经幡走了一圈,铜铃“叮铃”的声音随着风飘远,每响一声,他就念一句祈福的经文,声音低沉而庄重,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肃穆起来。
孙思邈站在草药棚前,正和药童们一起整理草药。他手里拿着一株刚成熟的黄芪,黄芪的根须粗壮,表面泛着浅棕色的光泽,他用手指轻轻掐了掐,根肉饱满,带着淡淡的药香。“这黄芪长得比在大唐时还好,看来雪域的水土适合它。”他笑着对身边的贡布说,“等立柱仪式结束,我们就可以用它给牧民们煮补药了,冬天喝了能抗寒。”
贡布走过来,手里拿着一束雪莲花,花瓣是淡紫色的,花蕊里还沾着晨露:“孙医师,这雪莲花是我今早从红山山腰采的,刚开的,用来泡酒最好,能治风湿。”他把雪莲花递给孙思邈,指尖不小心碰到了孙思邈的手,两人都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——以前的争执早已烟消云散,现在的他们,更像并肩同行的朋友。
太阳渐渐升高,金色的阳光洒在工地上,将柏木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松赞干布带着文武大臣从逻些城赶来,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并肩走在前面,她们的藏袍上绣着金线,走动时,衣摆扫过地面的青草,带起一串露珠。百姓们自发地围在工地周围,手里捧着哈达和青稞酒,脸上满是期待——他们知道,这根立柱立起来,寺庙就离建成更近了一步,以后的日子,会有佛音,有医馆,有更多的温暖。
第二节 立柱时刻:号子声与锅庄舞
辰时三刻,立柱仪式正式开始。王匠师手持木尺,先在柏木的底部量了三次,又在柱础上画了一道红线,大声说:“柱正,础平,可立!”话音刚落,八个吐蕃工匠和四个大唐工匠一起走到柏木旁,他们都穿着厚实的羊皮袄,腰间系着麻绳,绳子的一端牢牢绑在柏木的顶端。达瓦站在最前面,手里拿着一个铜哨,他深吸一口气,吹响了哨子——“嘀——”的一声,工匠们齐声喊起了号子。
“嘿哟!起哟!”
“嘿哟!立哟!”
号子声低沉而有力,像从大地深处传来的回响。工匠们的脚步整齐地踏在地上,每踏一步,柏木就往上抬一寸。达瓦的脸涨得通红,额头上的青筋凸起,他盯着柏木的垂直度,嘴里不停地喊着:“往左一点!再往左!”王匠师则拿着水平仪,站在柱础旁,眼睛紧紧盯着仪上的水泡:“再直一点!快了!快了!”
周围的百姓都屏住了呼吸,卓玛攥着衣角,手心都出了汗;杏花抱着刚烤好的青稞饼,忘了递出去;贡布法师手里的铜铃停在半空,眼神里满是紧张。直到柏木的底部稳稳地落在柱础上,王匠师大喊一声“正了!”,百姓们才爆发出欢呼声,哈达像雪片一样扔向工匠们,青稞酒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
松赞干布走上前,从侍从手里接过一碗青稞酒,递给达瓦:“达瓦大叔,辛苦你们了!这碗酒,敬你们为吐蕃建下的第一根柱!”达瓦双手接过酒碗,仰起头一饮而尽,酒液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上,他抹了一把,笑着说:“赞普殿下,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,是王匠师教我们的法子,是大唐工匠帮我们的忙,更是大家一起的心血!”
王匠师也接过酒碗,他喝得很斯文,却也喝得干净:“达瓦大叔说得对,这根柱子,是吐蕃的柏木,大唐的技法,还有大家的心意,少了一样都立不起来。”说着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木剑,递给达瓦的孙子阿吉——阿吉才六岁,穿着小小的藏袍,一直跟在达瓦身边看立柱。“这是我用剩下的柏木做的,送给你,以后长大了,也做个好木匠,给吐蕃建更多结实的房子。”
阿吉接过木剑,高兴得蹦了起来,举着剑在人群里跑:“我要建房子!建比寺庙还大的房子!”百姓们看着他的样子,都笑了起来,连松赞干布都忍不住揉了揉阿吉的头。
就在这时,一阵六弦琴的声音传来。卓玛抱着她的六弦琴,坐在一块青石板上,指尖拨动琴弦,弹出了吐蕃牧歌的调子。她的声音清亮,像山涧的泉水:“红山的雪化了,拉萨河的水涨了,柏木柱立起来了,百姓的日子甜了……”
随着歌声,十几个吐蕃青年男女从人群里走出来,开始跳锅庄舞。男人们穿着黑色的藏袍,腰间系着宽腰带,踏脚时,靴子上的铁钉踩在地上,发出“踏踏”的响声;女人们穿着彩色的藏袍,甩动着袖子,藏袍的下摆像绽放的花朵,银饰的“叮当”声和六弦琴的调子完美契合。他们围着刚立起的柏木,一圈圈地跳着,舞步从慢到快,歌声从低到高,连大唐工匠们都被感染了,李二拉着赵三,笨拙地跟着踏脚,虽然动作不协调,却笑得格外开心。
文成公主看着眼前的景象,对尺尊公主说:“你看,这就是最好的交融——不是刻意的拼凑,而是自然而然的欢喜。”尺尊公主点头,她想起天竺的梵音,大唐的小调,还有吐蕃的牧歌,这些不同的声音,此刻都融在立柱的庆典里,像一首温暖的歌。
卓嘎拉着杏花,也加入了跳舞的队伍。杏花跟着卓嘎的动作,甩动着唐装的袖子,虽然没有藏袍的飘逸,却也有别样的灵动。卓嘎笑着说:“杏花姐,你跳得真好!下次我教你跳‘弦子舞’,比锅庄舞更温柔。”杏花喘着气,脸上满是汗水,却笑得灿烂:“好啊!我也教你唱大唐的《茉莉花》,你肯定喜欢!
第三节 烟火盛宴:手抓肉与奶渣糕
正午时分,庆典的宴席在工地旁的草地上铺开。吐蕃百姓们从家里带来了铜锅和木盘,大唐工匠们则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瓷碗,大家围坐在火塘边,分享着准备好的食物,烟火气在红山脚下弥漫开来。
拉姆阿妈负责烤手抓羊肉。她把一只整羊架在火塘上的铁架上,羊身上涂满了盐和辣椒粉,炭火的火苗舔着羊肉,油脂顺着铁架滴下来,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,肉香很快就飘满了整个草地。她手里拿着一把长柄刀,时不时给羊肉翻面,刀刃划过烤得金黄的羊皮,能听到“咔嚓”的脆响。“这是我家最肥的羯羊,养了三年,今天特意杀了给大家吃!”拉姆阿妈的声音洪亮,她割下一块羊腿肉,递给身边的大唐大臣:“大人,您尝尝,我们吐蕃的羊肉,没有膻味,越嚼越香!”
大臣接过羊肉,用手撕开一块,放进嘴里——羊肉的外皮酥脆,里面的肉却很嫩,盐和辣椒粉的味道刚好,没有一点膻气,只有羊肉本身的鲜香。他忍不住竖起大拇指:“好吃!比大唐的烤羊肉还地道!”
不远处,卓玛和几个小姑娘正忙着做奶渣糕。她们把新鲜的牦牛奶倒进铜盆里,放在火塘边加热,等牛奶凝结成奶渣,再加入青稞粉和小块的酥油,用手揉成面团,捏成小饼的形状,放在石板上烤。奶渣糕刚烤好时,表面是金黄色的,咬一口,外脆里软,奶渣的酸香和酥油的醇厚在嘴里散开,还有青稞粉的颗粒感,口感格外丰富。卓玛拿起一块刚烤好的奶渣糕,递给尺尊公主:“公主,您尝尝,这是我和阿妈一起琢磨的新做法,加了一点蜂蜜,更甜了。”
尺尊公主接过奶渣糕,指尖碰到温热的饼面,心里暖暖的。她咬了一小口,蜂蜜的甜香刚好中和了奶渣的酸味,青稞的清香在舌尖萦绕,她笑着说:“卓玛的手艺真好,以后寺庙建成了,你可以在医馆旁边开个小铺子,卖奶渣糕,肯定很多人买。”卓玛的脸一下子红了,低下头,手里的奶渣糕捏得更紧了。
孙思邈和贡布坐在一块大石头上,面前放着一碗雪莲花泡酒。酒是用青稞酒泡的,里面泡着几朵新鲜的雪莲花,花瓣在酒里舒展着,像在跳舞。贡布给孙思邈倒了一碗:“孙医师,这酒能驱寒,你在大唐没喝过吧?”孙思邈接过酒碗,抿了一口,酒液带着淡淡的药香和青稞的醇厚,下肚后,胃里暖暖的,很舒服。“好喝!”他赞叹道,“等冬天来了,我们可以给牧民们泡一些,让他们抵御风寒。”
贡布笑着点头,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羊皮袋,里面装着风干的牛肉干:“这是我去年冬天做的,用盐和花椒腌过,能放一年。你尝尝,饿的时候吃一块,顶饿。”孙思邈拿起一块牛肉干,放在嘴里嚼着,牛肉干很有嚼劲,越嚼越香,还有花椒的麻味,很开胃。“比我们大唐的肉脯有味道!”他说,“回头你教我怎么做,我也给我在大唐的徒弟寄一些。”
李二和达瓦坐在火塘边,正分享着一壶酥油茶。李二手里拿着一块青稞饼,蘸着酥油茶吃,含糊地说:“达瓦大叔,您上次教我的缝靴子的法子,我试着做了一双,虽然不好看,但是很结实。”达瓦笑着说:“慢慢来,做靴子要用心,就像建寺庙一样,急不得。下次我教你用羊毛做鞋垫,冬天穿更暖和。”
赵三则和几个吐蕃工匠围着一个铜锅,锅里煮着青稞粥,粥里加了酥油和小块的羊肉,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赵三用勺子舀起一勺粥,吹了吹,喝了下去,满足地叹了口气:“这粥比我们大唐的小米粥还香!要是加一点大唐的红枣,肯定更好喝。”旁边的吐蕃工匠立刻说:“下次你带红枣来,我们一起煮!”
夕阳西下时,宴席还在继续。火塘里的火渐渐弱了,变成了通红的炭火,映着每个人的脸。卓玛又弹起了六弦琴,这次唱的是文成公主教她的大唐小调,虽然歌词咬得不太准,却唱得格外认真。百姓们跟着哼唱,声音里满是欢喜,连远处的牦牛都抬起头,像是在听这温暖的歌声。
尺尊公主站在刚立起的柏木旁,伸手抚摸着木材的表面,柏香从指尖传来,带着阳光的温度。她看着眼前的景象——百姓们的笑脸,工匠们的谈笑声,歌舞的身影,还有弥漫在空气中的烟火气,突然觉得,这座寺庙不只是一座建筑,更是一个“家”,一个容纳了不同文明、不同信仰、不同生活的家。
松赞干布走到她身边,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轻声说:“你想要的‘佛光永照’,不只是金印上的字,更是眼前的景象——百姓安乐,文化交融,这才是真正的佛光。”
尺尊公主点头,眼里泛起了泪光。她知道,这根柏木柱立起来的,不只是寺庙的框架,更是吐蕃与大唐、天竺友谊的根基,是雪域文明走向交融的起点。而那些融入其中的歌舞、美食、生活细节,就像柏木上的纹路,深深浅浅,都刻着“温暖”与“共生”的印记。
夜色渐深,百姓们渐渐散去,工地上只留下几个守夜的工匠。火塘里的炭火还在燃烧,偶尔发出“噼啪”的响声,经幡在夜风中飘动,铜铃的声音断断续续,像是在为这一天的热闹收尾。达瓦躺在柏木旁的草地上,看着天上的星星,嘴角带着笑——他仿佛已经看到,这座寺庙建成后,佛音缭绕,医馆里满是百姓的笑脸,孩子们在寺庙前的草地上跳着锅庄舞,手里拿着奶渣糕,笑得格外开心。
而这一切,都从这根立起的柏木柱开始,从这一场充满烟火气的庆典开始,从每一个为了“更好的日子”而努力的人开始。雪域的梵音,在这一刻,仿佛已经在红山脚下响起,温柔地,长久地,回荡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