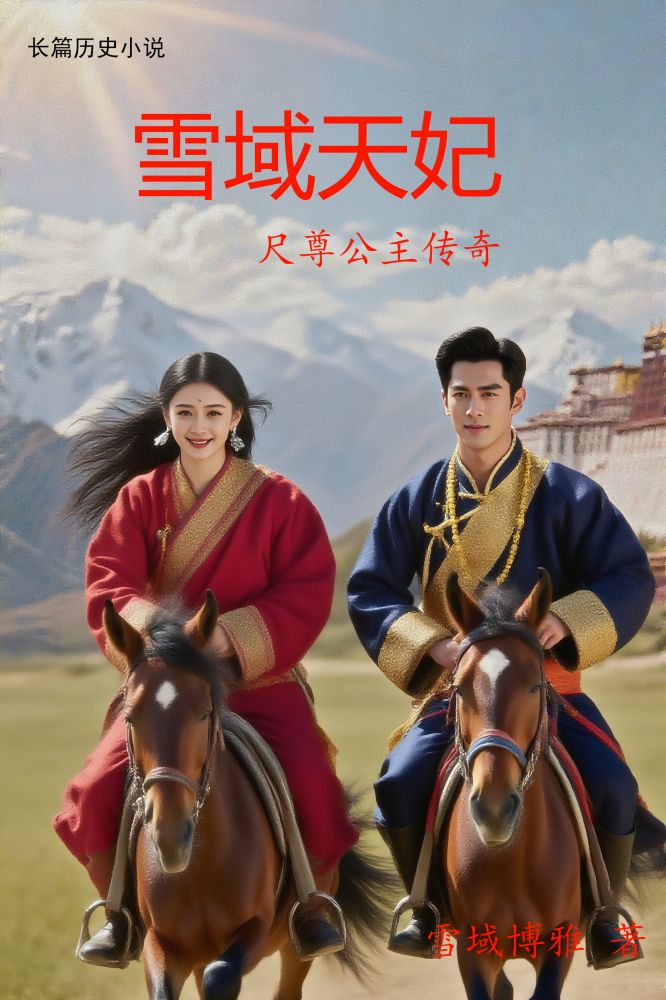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连载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
第一卷·迦舍末罗的红
第八章 长安的风烟
吐蕃的春天,是从融雪的滴答声里来的。
布里库提站在绿绒苑的廊下,看着檐角的冰棱化成水珠,一滴滴落在青石板上,晕开小小的湿痕。达拉正蹲在豌豆地里,小心翼翼地给新抽的嫩芽搭架子,绿裙的裙摆扫过泥土,沾了些带着草香的湿泥——那是从迦舍末罗带来的种子,如今在逻些城的土地里,长出了和家乡一样的嫩绿。
“公主,唐朝的使者到了!”
禄东赞的声音带着罕见的轻快,他大步穿过绿绒蒿丛,黑氆氇大袍的下摆沾着雪水融化的泥点,手里捧着个鎏金的盒子,阳光照在上面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“唐太宗派来的,说是给您的礼物。”
布里库提的指尖轻轻一颤。唐朝的礼物?她接过盒子,入手沉甸甸的,打开的瞬间,一股淡淡的墨香混着檀香漫出来——里面是一卷《女诫》,用蜀地的锦缎装裱,首页盖着唐太宗的“贞观之印”,字迹圆润有力,是典型的中原书法。
“使者说,这是长孙皇后亲手抄写的。”禄东赞的刀疤在阳光下泛着光,“还说,陛下邀请您和赞普派的使团一起去长安,看看唐朝的春天。”
《女诫》的纸页细腻,长孙皇后的字迹里带着股温润的力量,不像吐蕃的经文那么凌厉,倒像加德满都佛堂里的梵文,藏着对女性的期许。布里库提的指尖抚过“卑弱第一”四个字,忽然想起母亲说的“女子的力量,不在强硬,而在柔韧”,原来相隔万里的两位女性,竟有这样相似的感悟。
“赞普同意了吗?”她抬头看向禄东赞,目光落在他腰间的蛇纹弯刀上——刀鞘上的铜钉被磨得发亮,显然刚从红宫议事回来。
“赞普说,让您做主。”禄东赞的语气里带着敬意,“他还说,若是您去长安,就把盟书里藏的‘新文字’带去,让唐朝的文人也看看,吐蕃的智慧不输中原。”
风从绿绒蒿丛里钻出来,吹得廊下的经幡哗哗作响。布里库提想起父亲的话:“迦舍末罗的红,要在雪山南北都开成花。”她把《女诫》放回盒子,鎏金的边角在阳光下闪着光,像颗跳动的星。
“我去。”她说,指尖在盒盖上轻轻一叩,“但我要带两样东西——吐蕃的青稞种子,还有迦舍末罗的优昙婆罗花籽。”
出发去长安的前三天,松赞干布在红宫为使团践行。殿里的壁画新补了几处,画的是唐蕃边境的互市场景,中原的丝绸和吐蕃的氆氇堆在一起,像两朵并蒂的花。大相(梅朵的父亲)坐在左侧,脸色依旧有些沉,但看着布里库提的目光,比上次祭祀时柔和了些。
“到了长安,少说话,多看看。”大相的声音里带着股别扭的关切,手里转着苯教的经筒,“唐朝的文人最会绕弯子,别被他们骗了。”
梅朵坐在父亲身边,绿绒蒿发簪在鬓角闪着光,她偷偷塞给布里库提一个小布包:“这是我阿爸的‘雪山盐’,长安的饭菜可能不合你胃口,就着吃。”布包里的盐粒粗糙,带着股淡淡的矿物味,像吐蕃的石头。
松赞干布最后举杯,赭红色的赞普袍在酥油灯下泛着光:“记住,你带去的不只是种子,是吐蕃的诚意。若是见到唐朝的公主,替我说声‘欢迎来雪山看看’。”他的目光落在布里库提发间的绿绒蒿簪上,忽然笑了,“说不定,以后逻些城的春天,会有长安的牡丹。”
离开逻些城的那天,珞巴部落的猎手们来送行。他们骑着马,举着长矛,矛尖上系着五彩的经幡,像一支护卫的仪仗。首领捧着一碗青稞酒,单膝跪地:“公主,我们在雪山垭口等您回来,给您猎最肥的雪豹!”
布里库提接过酒碗,一饮而尽。酒液辛辣,却在喉咙里化成了暖意,像无数双手在推着她往前走。马车驶离红山时,她回头望了一眼,绿绒苑的豌豆地在晨雾里泛着嫩绿,梅朵站在宫殿的台阶上,正对着她挥手,狼头簪的影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。
前往长安的路,比来时翻越雪山更漫长,却也更热闹。渡过金沙江后,中原的风物渐渐清晰——稻田里的秧苗绿得像翡翠,村庄里的瓦房错落有致,与吐蕃的土房截然不同。驿站里的驿卒穿着青色的官服,见了吐蕃使团,虽有好奇,却并无敌意,端来的茶水带着茉莉的清香,比酥油茶多了几分雅致。
“公主,您看那座桥!”达拉扒着车窗,手指着远处的石拱桥,桥栏上刻着精美的龙纹,“比加德满都的石桥好看多了!”
布里库提笑着点头。她正在看随行的唐朝使者带来的《两京杂记》,里面说长安有“八街九陌”,朱雀大街宽得能并排走二十匹马,街上的胡商比吐蕃的还多,卖着波斯的香料、印度的宝石,像个装着全世界的盒子。
进入长安的那天,正是清明。朱雀大街上挤满了人,百姓们穿着绸缎的衣裳,孩子们手里举着纸鸢,风筝的尾巴在风里飘,像吐蕃的经幡。街道两旁的店铺挂着幌子,酒肆里传来猜拳的吆喝,绸缎铺的伙计正给胡商展示新到的蜀锦,热闹得像加德满都的神节。
“那就是皇城!”使团里的吐蕃武士指着远处的宫墙,声音里带着惊叹。宫墙是用黄土夯成的,高得像座小山,城门上的金钉在阳光下闪着光,比红山宫殿的铜钉更显威严。
唐太宗在太极殿接见了他们。殿里的梁柱上雕着龙,屋顶的琉璃瓦泛着青色的光,与吐蕃的酥油灯不同,这里的宫灯用的是鲸油,亮得没有一点烟火气。唐太宗坐在龙椅上,穿着明黄色的龙袍,面容威严却带着笑意,目光扫过布里库提时,带着几分审视,也带着几分温和。
“迦舍末罗的公主,一路辛苦了。”他的声音洪亮,像吐蕃的法号,却多了几分书卷气,“听说你带来了雪山的种子?”
布里库提弯腰行礼,动作是吐蕃的屈膝礼,却又带着迦舍末罗的柔和:“托陛下的福,种子都好好的。吐蕃的青稞能耐寒,或许能在长安的土地上长出新的味道。”她从锦囊里掏出优昙婆罗的花籽,用锦缎包着,递上前去,“这是迦舍末罗的花,三千年一开,陛下若不嫌弃,可种在御花园里。”
唐太宗接过花籽,放在鼻尖闻了闻,忽然笑了:“好个‘新的味道’。朕听说,你在吐蕃教百姓捏莲花朵玛?”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大臣,“房玄龄,你看这位公主,倒比我们的言官更懂‘融合’。”
站在左侧的房玄龄上前一步,穿着紫色的官袍,须髯花白,却精神矍铄:“陛下说得是。尺尊公主带来的不只是种子,是让雪山与中原对话的话本。”他的目光落在布里库提发间的绿绒蒿簪上,“这松石倒是别致,像极了终南山的翡翠。”
布里库提的心轻轻一动。房玄龄!她在《西域志》里见过他的名字,说他是唐朝的“贤相”,能在皇帝发怒时,用一句诗化解纷争。此刻见他目光温和,果然像书里写的那样,有股让人安心的力量。
接见结束后,唐太宗让长孙皇后的侄女,平阳公主李秀宁陪布里库提游览长安。平阳公主穿着戎装,却并不显粗犷,腰间的佩剑上镶着宝石,像朵开在剑鞘上的花。她带着布里库提去了西市,指着胡商的摊位笑道:“你看,这里的波斯地毯,和吐蕃的氆氇是不是很像?”
西市的热闹超出了布里库提的想象。胡商在用粟特语讨价还价,卖糖人的小贩捏出的糖佛,竟有几分尼泊尔的风格,穿绿袍的文人正对着幅西域地图争论,说葱岭以西的雪山里,住着会飞的神人。
“他们说的,是不是迦舍末罗?”达拉指着那些文人,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平阳公主笑了:“说不定是。长安就是这样,全世界的故事都在这里发芽。”她忽然压低声音,“我姑姑(长孙皇后)说,陛下有意让文成公主去吐蕃和亲,只是还在犹豫——他怕公主受不了雪山的苦。”
布里库提的心猛地一跳。文成公主!她终于听到了这个名字,像颗投入湖心的石子,荡起圈圈涟漪。她想起松赞干布说的“长安的牡丹”,忽然觉得,这朵牡丹若真能开在逻些城,定会和绿绒蒿相映成趣。
在长安的日子,布里库提去了国子监,看中原的学子读《诗经》,听他们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念“关关雎鸠”,竟和吐蕃的歌谣有几分相似的韵律;她去了慈恩寺,见玄奘法师刚从西域回来,正在翻译佛经,梵文的贝叶经摆在案上,和她带来的《十万颂》放在一起,像对久别重逢的朋友。
离别的前一天,唐太宗在曲江池设宴。池边的柳树抽出新绿,像少女的长发,仕女们划着画舫,唱着江南的小调,歌声里带着水汽的温柔。席间,房玄龄提议让布里库提用藏文写几个字,她提笔在桑皮纸上写下“唐蕃永好”,字迹里既有吐蕃的硬朗,又有迦舍末罗的圆润。
“好字!”唐太宗拿起纸,对着阳光看,“既有雪山的骨,又有流水的韵。朕把它刻在石碑上,立在长安的城门口,让往来的人都看看。”
布里库提站起身,举杯敬向唐太宗:“臣女有个请求——想带些长安的牡丹种子回去,种在逻些城的绿绒苑,让吐蕃人知道,中原的花,和雪山的花一样美。”
唐太宗笑着点头:“准了。再给你些蚕种和纺车,让吐蕃的女子也能穿上自己织的丝绸。”他的目光变得深邃,“朕知道,和亲之路不易,但朕相信,你和未来的文成公主,会让雪山和中原的风,吹向同一个方向。”
离开长安时,平阳公主送了布里库提一柄匕首,鞘上刻着“长乐未央”四个字。“这是我征战时用的,”她说,“若在雪山遇到难处,就看看它——女子的勇气,不输男儿。”
马车驶离朱雀大街时,布里库提最后望了一眼长安的城郭。阳光下的皇城像座金色的山,西市的胡商还在吆喝,慈恩寺的钟声隐约传来,混着风里的花香,像一首未完的歌。她怀里的牡丹种子微微发烫,像揣着整个长安的春天。
使团的武士们唱起了吐蕃的歌谣,歌声里混着中原的调子,竟意外地和谐。布里库提打开车窗,看见路边的田里,有农人正在播种,新翻的泥土里,藏着和吐蕃一样的希望。
她知道,从长安带回的不只是种子和纺车,是让两种文明相遇的钥匙。而那尚未谋面的文成公主,或许此刻也在长安的某个庭院里,看着牡丹花开,想象着雪山的样子——她们的传奇,将在不久的将来,在逻些城的红山下,交织成一首跨越万里的诗。
(未完待续)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