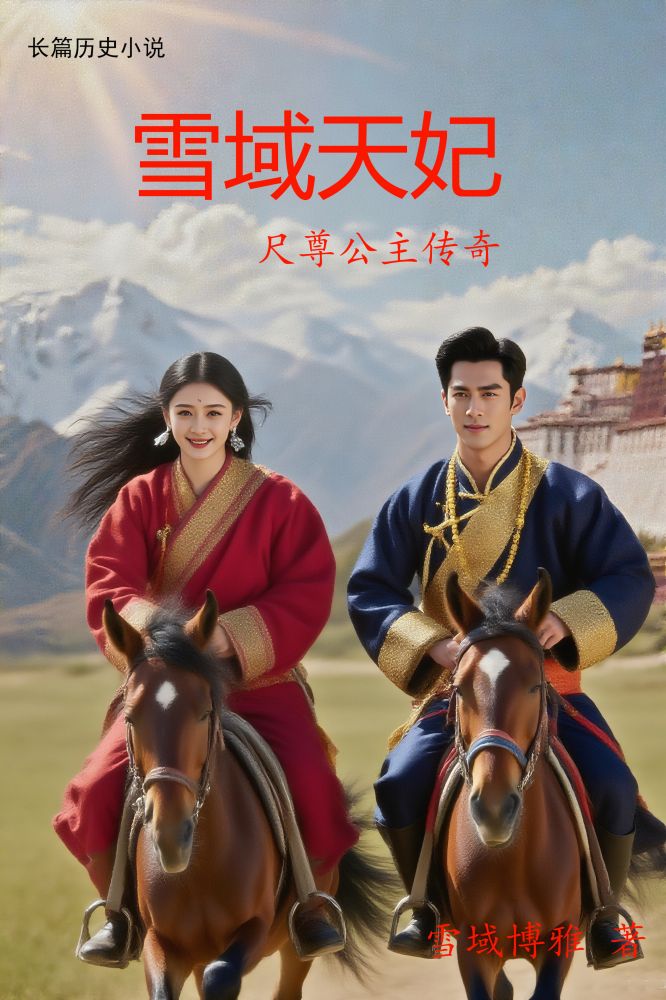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连载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 第二卷·小昭梵音 第二章 雪色与火光
藏历十月的雪来得猝不及防。初雪落时,万经阁的飞檐还挂着秋末的最后一串青稞穗,雪片沾在穗子上,像给金黄的念珠串上了颗颗碎银。梅朵推开门时,正撞见尺尊用藏地的牦牛毛扫帚扫经阁前的台阶,扫帚尖扬起的雪粉落在她的氆氇袍上,转眼就化成了水,洇出一小片深色的痕。
“得糊窗了。”尺尊呵着白气说。万经阁的窗棂是中原样式的格扇,夏天通风极好,到了寒冬却挡不住穿堂风。去年用桑皮纸糊的窗,经不住腊月的寒风,今年文成公主早让人备了中原的宣纸,又掺了吐蕃的牦牛皮胶,说这样“既透光,又抗冻”。
梅朵抱着摞氆氇布跑来,布上是她和吐蕃孩童绣的纹样:苯教的九字真言、佛教的莲花座、中原的福字结,针脚歪歪扭扭,却把三种符号绣成了一团,像朵被雪压弯的八瓣梅。“阿姐说,用这个糊窗,风就钻不进来了。”
大相正指挥人在经堂中央垒火塘。火塘用的是吐蕃的青石板,边缘却让唐朝工匠錾了圈缠枝纹,纹路上还嵌着波斯的琉璃珠,雪光反射上去,珠子里仿佛盛着细碎的火焰。“苯教的《火经》里讲,火塘是家的心脏,”他往塘里添了块阿里带来的波斯无烟煤,“得让这颗心一直热着。”
阿里扛着个铜制的火盆进来,盆沿刻着阿拉伯文的“安宁”。“这是撒马尔罕的手艺,”他用藏语比划着,“底下的镂空能漏灰,上面的花纹能挡风,在沙漠里过夜全靠它。”他把火盆放在经卷架旁,又从布袋里掏出几块西域的香料木,“烧这个,烟是香的,还能防蛀虫。”
那烂陀寺的僧人正往经卷间塞艾草包。艾草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,晒干后捆成小束,散发着清苦的香气。“《医方明》里说,艾草能驱寒邪,”他把藏地的雪莲花瓣混进艾草里,“加上这个,连高原的寒风都得绕着走。”
文成公主在调试新做的暖炉。炉胆是中原的铸铁,外层裹着吐蕃的羊皮,提手处缠着波斯的金线,炉盖上还让梅朵用红绳系了个中原的络子。“这叫‘三暖合一’,”她笑着拧开炉盖,里面烧着的是吐蕃的牦牛粪饼混着中原的炭,“铁胆保热,羊皮隔凉,金线……是好看。”
雪越下越大,经堂里却渐渐暖了起来。火塘的火苗舔着青石板,映得周围的经卷封面发亮:藏文的《丹珠尔》烫着金,汉文的《道德经》镶着蓝,梵文的贝叶经泛着蜜色的光。梅朵趴在窗台上,看外面的雪给万经阁的金顶蒙了层白,忽然指着窗纸上的绣纹笑:“你们看,苯教的雍仲符号被雪映着,像不像中原的太极在转?”
众人凑过去看,果然,雪光透过氆氇布上的针脚,把雍仲的“卍”字和太极的阴阳鱼照得重叠了,旋转的纹路在墙上投下流动的影子,竟像朵不停开合的花。“佛陀说‘诸行无常’,”那烂陀寺的僧人合掌,“原来变化里藏着不变的理。”
傍晚时分,雪停了。大相提议去寺后的温泉煮茶。那处温泉是吐蕃的圣泉,泉眼周围的石头被历代朝圣者摸得发亮,上面刻着藏文的“暖”、汉文的“温”、梵文的“热”。阿里提着个铜壶,里面装着波斯的红茶饼,说要煮“七味茶”——泉水是圣泉的,茶饼是波斯的,再丢进吐蕃的酥油、中原的姜片、印度的豆蔻、西域的葡萄干、苯教的甘露丸。
泉眼咕嘟咕嘟冒着泡,铜壶里的茶汤渐渐染上琥珀色。梅朵蹲在泉边,看雪水顺着石头缝流进泉里,转眼就化成了热气。“雪是天上的水,泉是地下的火,”她用树枝搅着水面的热气,“碰到一起,就成了暖的。”
文成公主舀了碗茶,递给那烂陀寺的僧人。“长安的冬天,百姓会在茶汤里加枣泥,”她说着,往自己碗里撒了把藏地的炒青稞,“吐蕃的法子,顶饱。”僧人呷了口,笑道:“印度的苦行僧在雪山修行,会把茶和菩提叶一起煮,说能清神。”
阿里的茶碗里飘着片红珊瑚,是他从波斯带来的护身符。“我们的先知说,温暖不止在火里,还在人心头,”他指着泉眼周围不同文字的刻痕,“你看这些字,笔画不一样,说的都是‘热’,就像不同的心,都在盼着暖。”
回经阁时,梅朵发现雪地上有串奇怪的脚印:大相的藏靴印旁边,是文成公主的中原绣鞋印,再往外是阿里的波斯皮靴印,最边缘是那烂陀寺僧人赤足踩出的浅坑。这些脚印在雪地里绕了个圈,最后都通向经堂的门,像条用不同步子踩出来的项链。
“就像五条路,”她数着脚印笑,“最后都走到了一个门口。”
夜里,经堂的火塘还在燃着。大相用藏文在桦树皮上写《火经》的注释,文成公主在旁边用汉文抄《礼记》里的“温良者,仁之本也”,阿里用芦苇笔在羊皮纸上画火盆的构造,那烂陀寺的僧人则在贝叶经上用梵文写《护火陀罗尼》。
梅朵坐在中间,手里拿着根线——中原的丝线、吐蕃的羊毛线、波斯的金线、印度的棉线,被她缠在手指上,绕成个五彩的球。“阿妈说,线断了就接不上了,”她把线头凑到火塘边烤了烤,轻轻一捻,不同的线竟融成了一股,“但只要愿意接,总能拧在一起。”
她用这股五彩线,在白天糊窗的氆氇布上补了个针脚。月光透过窗户,把那个小小的针脚照得发亮,像雪地里的一颗星。
第二天清晨,梅朵推开经堂的门,发现昨夜的积雪上,有只不知名的鸟留下了串爪印,从泉眼一直通向万经阁的屋顶。屋顶的雪被阳光晒得微微融化,金顶的光芒穿透雪雾,在经堂的墙上投下一道暖融融的光,恰好落在那卷《万经合璧》上。
经卷的空白页上,不知何时多了片雪花化成的水痕,形状像朵正在绽放的花。大相用指尖蘸了点水痕,在旁边写了个藏文的“热”,文成公主接过去写了汉文的“暖”,阿里写了阿拉伯文的“نور”(光明),那烂陀寺的僧人写了梵文的“ताप”(温暖)。
四种文字围着那朵水痕花,在晨光里像四颗星,照着同一个花心。
梅朵忽然跑去泉边,捧了把带着热气的泉水回来,轻轻洒在经卷旁的花盆里。花盆里是之前用七种河水养出的莲花苗,此刻正顶着点薄雪,抽出了片新叶。“雪会化的,”她摸着新叶上的绒毛,“就像冷总会过去,暖总会来的。”
火塘里的余烬还在发热,把周围的经卷烘得带着松烟香。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泛着银辉,经堂的炊烟直直地升向天空,与雪后的云缠在一起。大相望着那缕烟,忽然想起苯教的《火经》里说:“火的魂会变成烟,飞到天上,告诉神,人间有暖。”
而此刻,这缕烟里,藏着中原的炭香、吐蕃的牛粪味、波斯的香料气、印度的菩提香,混在一处,往天上飘去。
梅朵把那团五彩线球放在火塘边,线球在余温里慢慢舒展,像颗正在呼吸的心脏。她想起昨夜大家说的话,那些不同的语言在火塘边盘旋,最后都变成了同一个意思:
“我们都在这儿,守着这团火。”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