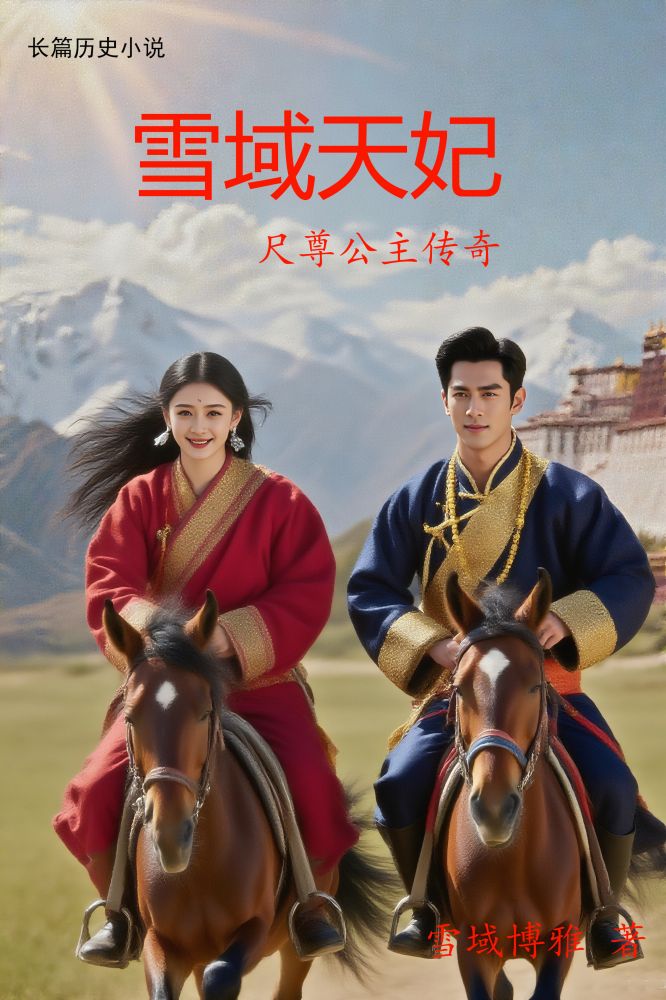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连载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 第二卷·小昭梵音 第十三章 声浪与回响
藏历十一月的法会,是万经阁最热闹的时节。寒风卷着经幡在广场上翻涌,赤红色的藏地经幡、明黄色的中原道旗、靛蓝色的波斯挂毯在风中相撞,边角扫过玛尼堆上的石片,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,像无数个小钟在同时摇晃。
梅朵抱着个铜铃跑过广场,铃身刻着苯教的“九宫八卦”,铃铛里却坠着颗中原的琉璃珠,跑动时珠子撞着铜壁,声音清透得像雪山融水。“阿爸说,法会要请‘万音’来聚,”她停在经堂门口,望着里面忙碌的人影,“连风的声音都算。”
大相正指挥着吐蕃乐师调试扎念琴。琴身是千年松木做的,琴弦却换了中原的蚕丝线,琴头雕刻的苯教神鸟嘴里,叼着根印度的孔雀羽。“苯教的《音经》里讲,最早的声音是风刮过骨笛的声,”他拨了下琴弦,音色里既有藏地的苍凉,又带着点中原丝弦的温润,“换了丝线,倒像神鸟学会了新调子。”
文成公主带来的长安乐师,正往古筝上缠藏地的牦牛毛。“中原的筝弦怕冻,”他笑着用藏语解释,指尖划过琴弦时,琴码上的波斯宝石片跟着颤,“加层毛,冬天弹起来更暖。”旁边的案几上,摊着他抄的《诗经》,其中“风有雅颂”四个字的空白处,被他画了扎念琴的简笔画。
阿里蹲在角落调试乌德琴。这把琴是他从波斯带来的,琴箱蒙着骆驼皮,琴颈却被吐蕃工匠刻上了藏文的“吉祥”。“我们的乐师说,乌德琴的声音像沙漠的驼铃,”他拨响琴弦,尾音拖得长长的,恰好和远处传来的藏地长号声重叠,“现在混着你们的号声,倒像两条河在唱歌。”
那烂陀寺的僧人带来了印度的七弦琴。他盘腿坐在氆氇上,指尖拨动琴弦时,嘴里哼起了梵文的《赞佛偈》。歌声不高,却像根无形的线,把周围的嘈杂声都串了起来——扎念琴的弹拨、古筝的流水音、乌德琴的颤音、长号的呜咽,竟在他的偈语里慢慢融成了一团。
法会的开场,是苯教的“神鼓”仪式。鼓手们戴着鹿角面具,鼓面蒙着牦牛皮,鼓身却用中原的朱砂画了太极图。他们踩着《斯巴卓浦》的节奏擂鼓,每声鼓响都震得经堂的铜铃叮当乱响,像在敲醒沉睡的土地。
紧接着,唐朝乐师奏响了《秦王破阵乐》。古筝的激昂混着藏地的骨笛声,竟把军乐的雄壮吹成了高原的辽阔。梅朵站在廊下,看乐师们的影子投在墙上,中原的广袖与藏地的氆氇袍在影子里重叠,像幅流动的画。
阿里的乌德琴突然加入进来。他弹的是波斯的《玫瑰颂》,旋律弯弯绕绕,像西域的藤蔓,缠着《秦王破阵乐》的棱角往上爬。那烂陀寺的僧人笑着拨动七弦琴,梵文的偈语跟着琴声起伏,竟让两种截然不同的调子生出了默契,像鹰和鸽在同一片天上盘旋。
“这才是‘万音和鸣’啊。”大相望着经堂中央,那里梅朵正带着孩童们摇铜铃。孩子们的铃音不成调,却像撒在声浪里的碎银,让所有复杂的旋律都变得清亮。他忽然想起苯教的传说:天地初开时,第一声雷是神的鼓,第一阵风是神的笛,万物的声音凑在一起,才唱出了世界的样子。
法会中段,是“百字诵”。大相用藏文念《苯教十万颂》,文成公主用汉文诵《金刚经》,那烂陀寺的僧人用梵文唱《心经》,阿里用阿拉伯文念《古兰经》的选段。四种语言在经堂里盘旋,起初像四条并行的河,后来渐渐漫过彼此的河岸,字音的尾韵缠在一起,竟分不清哪句是藏语,哪句是汉文。
梅朵听不懂这些经文,却觉得这些声音像极了她听过的自然之声:藏文的顿挫像雪山崩裂,汉文的平缓像黄河奔流,梵文的婉转像恒河涟漪,阿拉伯文的弹舌像沙漠热风。她忽然跑到经堂外,对着远处的雪山大喊了一声——她的声音很轻,却在山谷里撞出一串回声,那些回声回来时,竟带着经堂里所有声音的影子。
“你们听!”她拉着文成公主跑到廊下,山谷的回声正一波波涌来,把藏文的、汉文的、梵文的、阿拉伯文的调子揉成一团,像块被阳光晒化的蜜糖,“山在学我们说话呢!”
那烂陀寺的僧人合掌笑道:“佛陀说,‘一切音声皆是陀罗尼’。原来山也懂这个理。”
阿里望着雪山,忽然用波斯语唱起了故乡的歌谣。那是首关于绿洲的歌,旋律里带着风沙的粗糙,可被山谷的回声润过之后,竟添了点藏地歌谣的悠远。大相跟着用藏语和了一句,文成公主用汉文接上,那烂陀寺的僧人用梵文哼起调子,四种语言的歌谣在风中纠缠,像四个不同模样的人,手拉手跳起了圈舞。
傍晚法会散去时,梅朵在经堂的角落捡到片被风吹落的贝叶。叶面上,不知是谁用竹笔蘸着酥油,画了个简单的乐谱——五条横线是中原的谱子,上面的音符却是藏文的“དེ་བ་”(善)、梵文的“सुख”(乐)、阿拉伯文的“سعادة”(幸福)。
“这是首没有调子的歌,”她把贝叶举给文成公主看,夕阳透过叶面上的纹路,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,“但每个字,都在说高兴的事。”
夜里,万经阁的经卷在风中轻轻翻动,发出的沙沙声像在延续白天的唱诵。大相在整理法器时,发现扎念琴的丝弦上缠着根中原的古筝弦,两根弦在月光里微微颤动,发出同一个音。
“原来不同的弦,也能唱出一样的声,”他轻声说,想起白天山谷的回声,那些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调子,最后都变成了同样的温暖,“就像不同的人,心里都装着一样的盼头。”
梅朵把那片贝叶夹进《万经合璧》,旁边放着她白天收集的声音——用陶罐装着的风声、用竹筒盛着的泉响、用羊皮袋裹着的经堂唱诵。她相信这些声音不会消失,就像相信雪会化成水,水会酿成泉,泉会映出天上的星。
天快亮时,她被一阵特别的声音吵醒。那是风穿过万经阁的窗棂,吹动经幡,撞响铜铃,又裹着远处雪山的回声,在经堂里盘旋。这声音里有藏地的鼓点、中原的琴音、波斯的歌谣、印度的偈语,还有她自己喊出的那声清亮的回声。
梅朵趴在窗边,看着第一缕阳光爬上经堂的金顶。那些声音在晨光里渐渐淡去,却像在空气里留下了看不见的线,把万经阁、雪山、经幡、每个人的心都连在了一起。
她忽然明白,所谓“万音”,从来不是声音的堆砌,而是所有声音都在说同一句话。就像此刻,风还在唱,经幡还在响,远处的泉眼还在咕嘟,所有的声音凑在一起,轻轻说:
“我们都在这儿,唱着同一首歌。”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