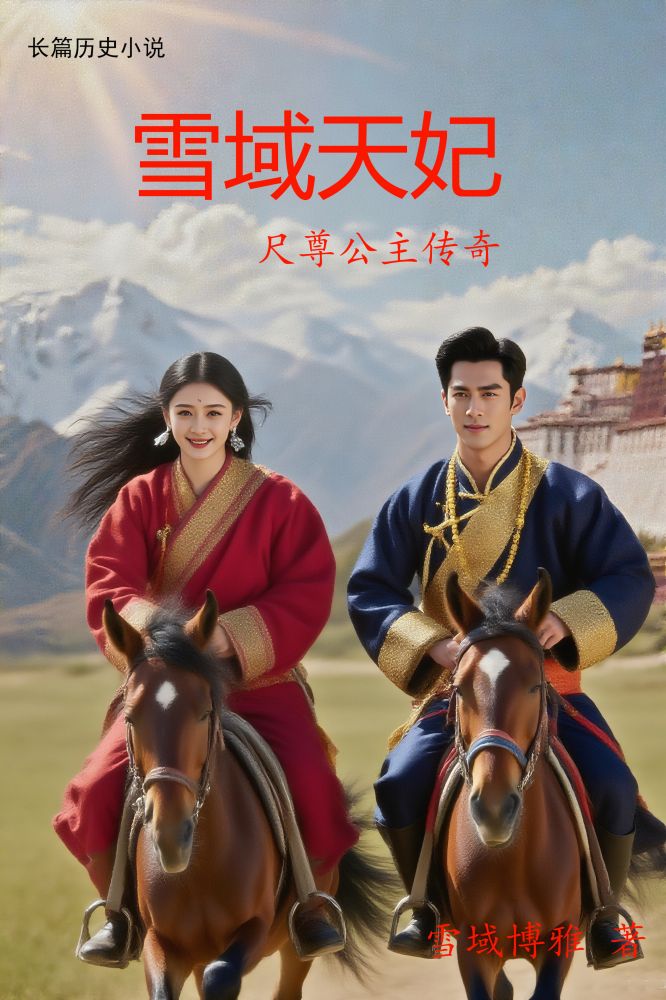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连载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第三卷 风的方向 第二章 琉璃光中的答案
藏历四月的雨,总带着股雪山融水的清冽。大昭寺的地基刚垒到第三层,就被这场连阴雨浇得停了工——吐蕃工匠用传统的夯土法筑墙,雨水一泡,墙根就软得像发面,上午垒的石块傍晚就塌了半尺。
“再这么下,雨季前怕是连佛台都立不起来。”吐蕃监工蹲在泥水里叹气,手里的木夯上还沾着湿土。他身边堆着中原工匠带来的石灰,按长安的法子,石灰掺沙子能防水,可高原的雨里带着雪粒,一冻,石灰层就裂得像龟甲。
尺尊公主披着尼泊尔氆氇斗篷站在工地上,斗篷边缘绣着尼泊尔帕坦古城的“孔雀窗”纹样,雨水打在上面,珠玑般的水珠顺着孔雀尾羽的纹路往下淌。她没穿吐蕃贵族的尖顶帽,而是裹着块尼泊尔手工织的羊毛头巾,露出的额间点着一点用藏红花汁画的“提拉克”——这是尼泊尔人祈福的印记,据说能驱散水祟。
“让工匠们先歇着吧。”她对监工说,声音里带着尼泊尔语特有的轻柔卷舌,“雨停前,我们得先弄明白,这地底下的水在说什么。”
她蹲下身,用手指戳了戳墙根的泥土。土是灰黑色的,攥在手里能挤出清凌凌的水,水里还混着些细碎的贝壳片。“这底下曾是湖。”尺尊忽然抬头,眼里闪着光,“你们看这些贝壳,是远古时候的湖床留下的。”
吐蕃工匠们面面相觑。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高原,只知道山是神山,却没想过脚下的土地曾是一片水。文成公主撑着油纸伞走过来,伞面是长安的青竹骨,蒙着吐蕃的牦牛皮,她弯腰捡起片贝壳:“《汉书·西域传》里提过,吐蕃山南曾有‘西海’,后来水退了才成了平原。看来这地基,正打在古湖床的软泥上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监工急得直搓手,“总不能把湖床挖穿吧?”
尺尊没说话,转身往工地旁的山坳走。雨雾里,她的身影像朵移动的蓝莲花——尼泊尔贵族的斗篷常用靛蓝染色,那是用喜马拉雅山的菘蓝草反复浸染十几次才有的颜色,雨越淋,蓝色越透亮。众人跟着她拐进山坳,发现那里藏着一汪泉眼,泉水从一块巨大的黑岩石下涌出来,石面上刻着苯教的“水纹咒”。
“你们看这石头。”尺尊指着黑岩,岩石表面光溜得像被打磨过,却在贴近水面的地方有圈圈凹槽,“雨水大的时候,泉水漫过凹槽,会顺着这些纹路流进旁边的沟壑——这是山神在教我们怎么引水呢。”
她让工匠取来绳子和木尺,趴在湿滑的岩石上量那些凹槽的深浅。尼泊尔女子从小跟着工匠学丈量,她的指尖比量绳还准,拇指和食指一掐,就报出了“深三寸,宽五寸,每尺降一分”的尺寸。“这是‘梯度槽’,”她解释道,“尼泊尔的神庙建在雪山脚下,地基常泡在融水里,我们就用这种槽把水引到远处的排水沟,既不堵水,又不冲地基。”
可问题还在软泥。就算引走了地表水,古湖床的淤泥一遇水还是会陷。吐蕃工匠主张往泥里填碎石,中原工匠说该打木桩,两种法子试了两天,不是碎石陷进泥里,就是木桩被冻裂的土地拱得歪歪扭扭。
夜里,尺尊坐在帐篷里翻图纸。她带来的尼泊尔《造像量度经》里,夹着张帕坦古城的地基剖面图:神庙的柱子底下,不是石头也不是木头,而是一层厚厚的“金刚砂”。那是喜马拉雅山的石英砂混合铁粉,用酥油和树脂拌匀,暴晒七七四十九天,硬得能抗住地震。
“可这里没有石英砂啊。”她对着地图叹气,手指划过吐蕃的山川——最近的石英矿在阿里,离这里有千里路。梅朵抱着暖炉凑过来,炉子里烧着尼泊尔的檀香木,烟味混着酥油茶的香,让帐篷里暖融融的。“我今天在山后看到好多碎骨头,”梅朵舔着嘴角的奶渍,“像是什么大动物的,硬得能划开石头。”
尺尊眼睛一亮。她知道,吐蕃的古湖边常有种“岩羊”,犄角坚硬如石,死后骨骼埋在土里,经过百年会钙化得像玉石。她连夜带着工匠往山后走,雨夜里,她额间的藏红花印记在火把下泛着红光,像颗引路的星。果然,山坳里的土层下,埋着厚厚一层钙化岩羊骨,敲开一块,断面亮晶晶的,硬度竟不输石英。
“有办法了!”尺尊举着骨块往工地跑,斗篷被树枝勾破了也没察觉。她让工匠把骨块碾碎,和吐蕃的红土、中原的石灰、尼泊尔的树脂混在一起,又往里面掺了些温泉口的硫磺——“硫磺能杀死土里的虫,免得它们啃食地基。”她边搅和灰浆边说,手指被石灰灼得发红也顾不上擦。
灰浆要发酵三天。这三天里,尺尊没闲着。她发现吐蕃工匠垒墙时,石块是随便堆砌的,中原工匠讲究“横平竖直”,却在高原的冻土上容易开裂。她想起尼泊尔的“错缝法”:大块石和小块石交替排列,像拼积木一样互相咬合,石缝里塞拌了酥油的草绳,既能缓冲冻土的膨胀,又能防水。
“你们看这朵花。”她摘下朵被雨打蔫的格桑花,花瓣一层压一层,却没一片是对齐的,“花能在风里站得稳,不是因为长得直,是因为互相抱着劲儿。”
三天后,发酵好的灰浆泛着珍珠母的光泽。工匠们按尺尊的法子,先在地基下挖了半人深的沟,铺上三层钙化骨砂,再用错缝法垒石墙,石缝里灌满灰浆。雨还在下,可这次,灰浆遇水非但不软,反而像生了根,把石块粘得死死的。
更妙的是引水的梯度槽。尺尊让人把山坳里的黑岩凹槽原样搬到地基四周,槽底铺着尼泊尔运来的防渗毡——那是用牦牛毛和喜马拉雅山的萱麻混纺的,浸过酥油后,水泼上去会像荷叶上的露珠一样滚走。雨水顺着槽沟流进远处的河沟,地基周围竟连个水洼都没积。
监工踩着刚垒好的墙根,跺了三脚,墙体纹丝不动。他蹲下来摸灰浆,已经硬得像块整体的石头,忍不住用藏语赞道:“这法子,比苯教的水咒还灵!”
尺尊只是笑着往灰浆里加了勺藏红花汁。在尼泊尔,建神庙时总要往灰浆里掺点吉祥草或花瓣,不是为了结实,是为了让石头也带着草木的生气。“石头会记得雨水的样子,”她说,“你对它好,它才会护着你。”
这天傍晚放晴了。夕阳把大昭寺的地基染成金红色,尺尊站在尚未完工的佛台上,望着远处的布达拉宫。她忽然想起离开尼泊尔时,母亲往她行囊里塞的那包“九宝土”——里面有喜马拉雅山的岩粉、恒河的河泥、菩提树下的净土、波斯的金沙……母亲说:“好的地基,要能装下天下的土,才能让神佛听得见万国人的祈愿。”
此刻,她脚下的地基里,既有吐蕃的红土,也有中原的石灰,有尼泊尔的树脂,还有岩羊的骨砂。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东西,在雨水里融成了一体,像块正在生长的玉石。
文成公主走过来,递给她块烤青稞饼,饼上抹了尼泊尔的酸奶:“你知道吗?长安的工匠说,你这法子,比他们的《营造法式》还多了三分灵劲儿。”
尺尊咬了口饼,酸奶的酸混着青稞的香,像回到了加德满都的早晨。“不是我聪明,”她望着正在垒墙的工匠们——吐蕃人用藏语喊号子,中原人哼着长安小调,还有几个跟着商队来的尼泊尔石匠,正用家乡话互相打趣,“是土地自己告诉我们的:不管是哪来的石头,只要心齐,就能站成山。”
梅朵突然指着地基旁的梯度槽喊:“水在唱歌呢!”众人侧耳听,雨水顺着凹槽流淌,经过不同深浅的槽口,竟发出“哆来咪”般的调子,像支天然的歌谣。
尺尊笑了,额间的藏红花印记在夕阳下像颗小小的太阳。她知道,这歌声里,有喜马拉雅山的雪水在说话,有长安的雨在应和,还有吐蕃的土地在静静听着——就像那些即将在大昭寺里共处的佛像,尼泊尔的工艺雕出的衣纹,中原的彩绘描出的眉眼,吐蕃的金箔贴出的佛光,最终都会在同一片屋檐下,被同一种香火照亮。
夜里,工匠们说,看到尺尊公主在地基旁撒了把种子。那是从尼泊尔带来的“七叶树”种子,据说种在神庙旁,树能长到顶天立地,树叶上的露珠会变成琉璃珠。
没人知道这是不是真的。但第二天清晨,人们发现那些梯度槽的凹槽里,不知何时被填满了细沙,沙上印着小小的脚印——像尺尊夜里蹲在那里,把每道槽沟都细细摸过一遍。而地基中央,那朵被她摘下的格桑花,不知被谁插在了灰浆缝里,花瓣上还沾着露水,在朝阳里轻轻颤动,仿佛在说:
这里的石头,已经醒了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