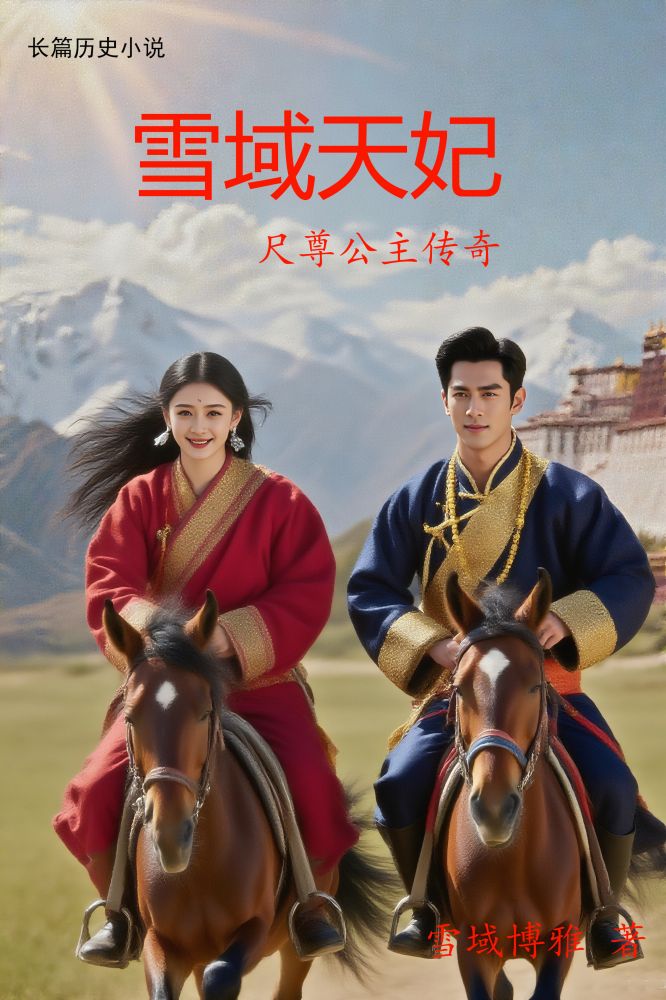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连载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第三卷 风的方向 第三章 雪山的负重
藏历六月,喜马拉雅山的雪线刚退到山腰,一支尼泊尔商队就踩着残雪进了吐蕃。领头的脚夫捧着个鎏金铜匣,匣子里装着尺尊公主母亲的亲笔信——信上用尼泊尔梵文写着:“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已从加德满都启程,随商队入藏,需经雪山七道关,望吾女亲往迎之。”
尺尊捏着信纸的手指微微发颤。那尊佛像,是尼泊尔工匠用百年旃檀木雕刻的,佛衣上镶嵌的七宝石是从印度、波斯、中原辗转搜罗来的,光打造就用了十二年。母亲在信里说:“此像需借雪山灵气方能安身,若途中有失,便是万劫不复。”
她连夜备了行装。除了吐蕃的防寒氆氇,还带上了尼泊尔的“五层靴”——靴底缝着牦牛皮、羊毛、萱麻、棉絮、丝绸,五层材料隔寒防潮,是喜马拉雅山民闯险关的利器。出发前,她让侍女取来一小罐“酥油蜜”,那是用尼泊尔蜂蜡、藏地酥油、印度砂糖熬成的,抹在嘴唇上能防裂,遇困时还能当干粮。
迎亲队伍走到第一道关“鹰嘴崖”就卡了壳。崖口宽仅三尺,两边是万丈深渊,唯一的通道是架在石缝间的藤桥。商队的头领愁眉苦脸地指着藤桥:“佛像装在樟木龛里,连龛带像重三千斤,这桥怕是承不住。”
吐蕃武士拍着胸脯说要拆了佛像分块运,被尺尊拦住了。她蹲在崖边观察藤桥,桥是用喜马拉雅山的“铁藤”编的,藤条粗如手臂,却在接头处用牛皮绳捆着,雨水泡久了有些松动。“拆像就是拆佛心。”她从行囊里掏出个小铜盒,里面装着尼泊尔工匠特制的“胶泥”——用高山柏树脂、青稞粉、牦牛血混合而成,晒干后硬如青铜。
“把松动的接头拆开,”她指挥脚夫,“用胶泥把藤条根根粘牢,再缠三层浸过酥油的牛皮。”自己则踩着五层靴走到藤桥中央,闭眼感受桥身的晃动。吐蕃武士吓得要拉她,却见她忽然睁眼:“桥的承重不在中间,在两边石缝的锚点。”
她让人往桥两端的石缝里楔入尼泊尔带来的“铁桦木”桩——这种木头比钢铁还硬,泡在水里百年不腐。桩子楔稳后,又在桥身下方加了八根斜拉绳,绳头系在崖顶的岩羊头骨上(按尼泊尔习俗,岩羊是山神的坐骑,能镇住山风)。等胶泥干透,她让二十个脚夫同时站上藤桥,桥身竟只微微下沉,连牛皮绳都没发出一丝异响。
“可以走了。”尺尊摘下头上的“孔雀冠”——那是尼泊尔贵族女子的头饰,冠顶的孔雀石能在阴雨天反光。她把冠子交给最前面的脚夫:“按冠上宝石的光亮走,亮处是实路,暗处有冰缝。”
过第二道关“雪盲坡”时,天突然转阴。高原的雪光在阴天最烈,能把人的眼睛灼出白翳。商队里已有三个脚夫捂着眼睛呻吟,吐蕃武士想点燃松烟遮雪光,却被尺尊拦住:“烟会引雪崩。”
她打开行囊,取出一叠尼泊尔“纱罗”——那是用喜马拉雅山的苎麻纤维织的,薄如蝉翼,却能过滤雪光。“把纱罗蒙在眼睛上,”她边说边给脚夫们分发,自己额间的“提拉克”印记在阴光下泛着暗红,“跟着我的脚印走,每步踏在我脚印前半掌的位置。”
原来她的五层靴底刻着细小的防滑纹,踩在雪地上会留下浅槽,槽里的雪化得慢,能看出路径。更妙的是纱罗,蒙眼后既能视物,又不刺眼,脚夫们都说:“像隔着雨看雪山,亮堂又不扎眼。”
最险的是第五道关“冰舌谷”。谷里的冰川每年夏天会融化成“冰舌”,表面看着平整,底下全是蜂窝状的融洞。佛像的樟木龛刚推进谷口,就听见“咔嚓”一声,龛底的冰面裂开了道缝。
吐蕃武士要往冰上撒碎石防滑,尺尊却让人取来商队驮的“青稞秸”。那是她特意让带来的,晒干的青稞秸韧性极好。“把秸杆铺在冰上,再浇点酥油。”她指挥着,“酥油遇冷会凝固,秸杆能咬住冰面,比碎石稳当。”
可冰舌太长,青稞秸不够用。眼看太阳偏西,再不走就要被封在谷里。尺尊忽然注意到冰面上的融水汇成了细流,正顺着一道隐秘的纹路往谷外淌。“这冰面有自己的路。”她蹲下来,用手指跟着水流的方向划了条线,“沿着这条水线走,融洞最少。”
果然,顺着水线铺青稞秸,走了半个时辰竟没再遇到冰裂。脚夫们啧啧称奇,尺尊却望着远处的雪山笑:“尼泊尔的老人说,雪山的水比谁都懂路,跟着它走,错不了。”
到第七道关“神佛山”时,商队的干粮快吃完了。山脚下的牧民说,山上有群野牦牛,见了人就撞,根本过不去。尺尊却让人杀了只随行的羊,取了羊血往佛像的樟木龛上抹了三道。“野牦牛是山神的护卫,见了佛血会让路。”她说着,从怀里掏出个小小的铜铃——那是尼泊尔“湿婆庙”的祈福铃,铃声能安抚野兽。
她走在队伍最前面,摇着铜铃,铃音在山谷里荡出层层回音。果然,刚到山腰,一群野牦牛从树林里冲出来,却在离樟木龛三丈远的地方停住了,为首的公牛盯着龛上的羊血,忽然掉头往山里走,群牛也跟着退了。吐蕃武士看得直咋舌:“公主的法子,比苯教的驱兽咒还灵!”
过了神佛山,就到了吐蕃与尼泊尔交界的“友谊桥”。桥对岸,尼泊尔商队的头领正捧着个锦盒等她。打开盒子,里面是佛像的“佛冠”,上面镶着颗鸽卵大的“月光石”——这是印度国王送的礼物,据说在暗处能发光。
“装冠子时要念‘三语咒’。”尺尊捧着佛冠,先用尼泊尔语念了段《金刚经》,又用藏语译了一遍,最后用中原的官话轻声说:“愿此像在吐蕃落地,如雪山常青。”她把佛冠戴在佛像头上时,月光石突然亮了起来,光芒透过樟木龛的缝隙渗出来,像给桥面上的脚印都镀了层银。
回程时,尺尊让脚夫们轮流讲故事。吐蕃脚夫说雪山神女的传说,尼泊尔脚夫讲加德满都的节日,中原商队的人说长安的市集。她自己则用尼泊尔语哼起了童年的歌谣,歌声像喜马拉雅山的溪流,带着冰碴子的清冽,却又软软的,能把坚硬的石头泡出暖意。
走到半道,她发现有个年轻的尼泊尔脚夫总掉队。一问才知道,他的五层靴底磨穿了,脚被冰碴子划得全是血。尺尊当即脱下自己的靴,塞给他:“我穿吐蕃的靴也能走。”自己则换上了双普通的藏靴,脚很快就冻得通红。
那脚夫捧着靴直哭,说:“公主的靴里有‘暖意石’(尼泊尔人把垫在靴底的羊绒团叫暖意石),我不能要。”尺尊却笑着指了指他的脚:“石头暖的是脚,人心暖的是路。你走得稳,佛像才能稳。”
藏历七月十五,等身像终于抵达拉萨。当樟木龛被抬进大昭寺的地基时,尺尊发现龛底沾着七道关的泥土——鹰嘴崖的红土、雪盲坡的白霜、冰舌谷的冰晶、神佛山的黑泥……她忽然明白母亲信里的话:“借雪山灵气”,不是指山的神力,是指那些踏遍雪山的脚印,那些不同语言的祈祷,那些互相搀扶的温度。
夜里,她坐在樟木龛旁,借着月光石的光亮绣经幡。幡面是尼泊尔的细棉布,她用藏地的羊毛线绣了藏文的“嗡嘛呢叭咪吽”,又用中原的丝线绣了汉文的“吉祥”,最后用金线在角落绣了朵尼泊尔的国花“杜鹃花”。风从窗缝里钻进来,经幡轻轻晃,像在说:
这尊佛像,早已不是尼泊尔的独产。它的衣纹里缠着吐蕃的风,它的宝石里映着中原的光,它的根基下,压着七道关的泥土,和无数双脚印的温度。
而尺尊额间的提拉克印记,在月光石的映照下,像颗小小的火种,正把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暖意,一点点焐进大昭寺的墙缝里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