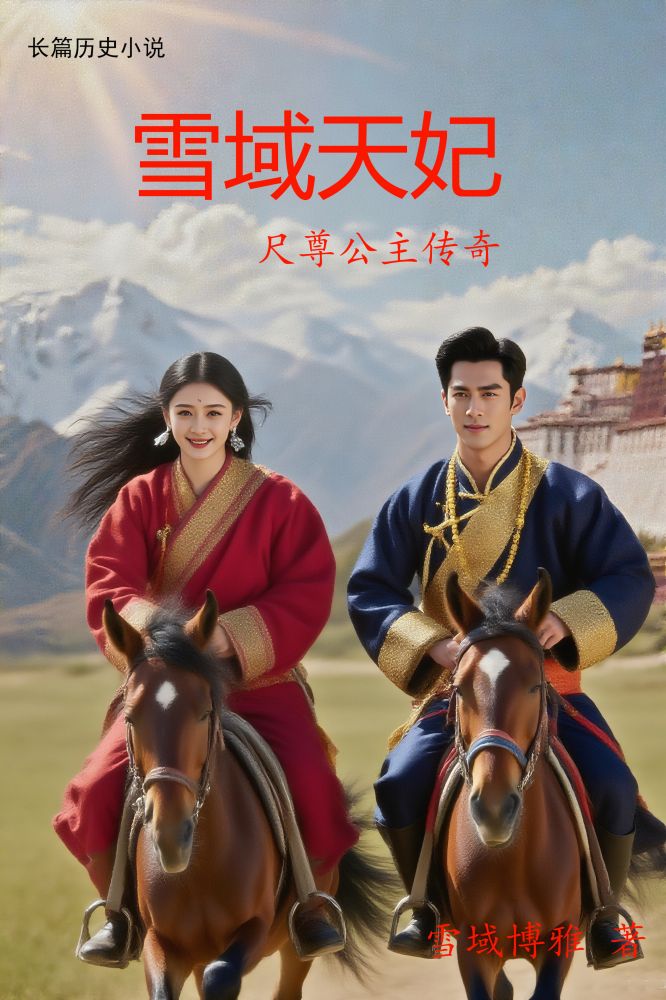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连载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第三卷 风的方向 第四章 双佛并立的光
藏历九月,大昭寺的金顶刚铺上第一片鎏金铜瓦,两尊佛像的安放就成了难题。尺尊公主带来的尼泊尔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,与文成公主带来的中原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,该谁居左谁居右?吐蕃贵族说该按尊卑排,中原工匠讲要依方位定,连苯教的大相都捧着《方位论》琢磨了三天,没个定论。
这天清晨,尺尊踩着露水去看佛像。尼泊尔的等身像立在临时佛龛里,佛衣的璎珞是用喜马拉雅山的绿松石串的,在晨光里泛着海一样的蓝;中原的等身像披着长安织的云锦袈裟,金线绣的莲花在阴影里也闪着光。两尊像隔着三丈远,却像两座互不相望的山。
“佛要是有灵,会自己选地方吧?”梅朵抱着只从山南捡来的小奶猫,猫爪在地上刨出浅坑,竟朝着两尊像中间的位置蹭了蹭。尺尊笑了,忽然想起尼泊尔帕坦古城的“双神龛”——湿婆与毗湿奴的神像总是面对面摆放,中间留着供信徒跪拜的空地,“神要看着人,也要看着彼此,才知道人心里的念想。”
她让人在大殿中央画了道线,线的两端各立一根柱子,柱顶架着块从尼泊尔运来的“透光石”——那是种能透过月光的石英岩,石面上刻着梵文的“卍”字。“先让月光选。”尺尊对众人说,“今夜月上中天时,看月光透过石上的字,落在哪尊像前。”
可夜里起了云,月光根本透不进殿门。吐蕃武士急得要去搬梯子捅云,被尺尊拦住了:“云是天的幔帐,它不想让月光来,自有道理。”她转身取来两盏灯,一盏是尼泊尔的酥油灯,灯座雕着迦楼罗鸟;一盏是中原的青瓷灯,灯壁绘着缠枝莲。“用灯光试试。”
两盏灯分别放在佛像前,灯芯都是尺尊亲手捻的——尼泊尔的用麻线,中原的用棉线,都浸过酥油。奇妙的是,酥油灯的光偏暖黄,照在尼泊尔佛像的绿松石璎珞上,竟映得整尊像像浸在夕阳里;青瓷灯的光偏青白,落在中原佛像的云锦袈裟上,仿佛敷了层晨霜。两束光在大殿中央交汇,形成片柔和的金白色,像块被阳光晒化的酥油。
“光都愿意凑在一起,佛怎么会不愿意?”尺尊指着那片交汇的光影,“就把两尊像往中间挪,让光的交汇处正好在佛台中央。”
可佛台的尺寸是固定的,两尊像并排放,就显得挤。中原工匠说要削窄尼泊尔佛像的基座,尼泊尔石匠立刻红了脸:“佛座是用加德满都的紫檀木做的,削一刀就是剜佛的脚!”
尺尊没说话,蹲在佛台边数地砖。大殿的地砖是按吐蕃的“九宫格”铺的,每块砖上都刻着不同的符号。她忽然指着中央那块刻着“日月同辉”的砖说:“把佛台往上升三寸,基座做成‘品’字形。”
原来她想让两尊像的基座错开,尼泊尔像的基座往前凸半尺,中原像的基座往后缩半尺,中间留出的空隙刚好能放下供桌。“就像两个人并肩走,谁也不挤着谁,还能手拉手。”她边画草图边说,笔尖蘸着清水在地上画,“尼泊尔的像面向东,迎日出;中原的像面向西,接月落。日出月落都照得到,才是圆满。”
更妙的是佛台的雕花。尺尊让尼泊尔工匠在吐蕃像的基座上刻喜马拉雅山的雪莲花,让中原工匠在中原像的基座上刻长安的牡丹,而两尊像相邻的侧面,刻的是同一朵格桑花——花瓣一半是尼泊尔的缠枝纹,一半是中原的云纹,“就像两朵花从一根根上长出来。”
安置佛像那天,来了好多人。吐蕃赞普带着贵族捧着哈达,文成公主穿着中原的锦袍,尼泊尔商队的人捧着家乡的杜松枝,连苯教的僧人都送来块刻着雍仲符号的石头,要垫在佛台底下。
尺尊亲自扶着佛像的底座,她的五层靴早已磨平了底,脚腕上还缠着治扭伤的草药——前几天为了量佛台尺寸,她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,却笑着说:“是佛在提醒我,做事要低头看路。”
当两尊佛像终于立在“品”字形佛台上时,阳光突然从金顶的铜瓦缝里漏下来,正好落在两尊像中间的格桑花雕刻上。众人都惊呼起来,只见那朵花的影子投在地上,竟像个藏文的“和”字。
“你看,佛早就答应了。”梅朵举着那只小奶猫,猫正盯着佛像的璎珞出神。尺尊摸着猫背笑,忽然发现自己额间的藏红花“提拉克”印记,被阳光照得映在佛台上,像颗小小的朱砂痣,落在两尊像中间的空隙里。
安置好佛像,该做供器了。吐蕃人用铜碗,中原人用瓷盘,尼泊尔人用银盏,各执一词。尺尊却让人取来三种材料:吐蕃的红铜、中原的高岭土、尼泊尔的白银,熔在一起铸成了套“三镶碗”——碗身是红铜,镶着白银的边,碗内壁挂着层青瓷釉。“盛酥油茶时,红铜能保温,白银不串味,青瓷不沾油。”她给众人演示,“不管是哪来的茶,都能装下。”
供桌上的酥油灯也有讲究。尺尊让人做了盏“转灯”,灯座是个能转动的轮子,轮上插着十二盏小灯——三盏尼泊尔的酥油灯,三盏中原的菜油灯,六盏吐蕃的牦牛油灯。“转起来的时候,光就混在一起了,分不清哪盏是哪的。”她说着转了转轮子,灯光在佛像脸上晃,像佛在微微眨眼。
这天夜里,尺尊坐在佛台前,看着两尊佛像的影子在墙上依偎在一起,忽然想起离开尼泊尔时,母亲给她讲的故事: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和丈夫湿婆吵架,把自己变成两半,一半在喜马拉雅山,一半在恒河边,可月光一照,两个影子还是会叠成一个。
“原来不管离多远,心连着,就分不开。”她从怀里掏出块小小的菩提叶,那是从尼泊尔菩提伽耶带来的,叶面上用梵文写着“众生平等”。她把叶子夹在两尊像中间的供册里,叶子的边缘正好压住藏文的经卷和汉文的偈语,像只手轻轻按着两本书的页码。
梅朵抱着毯子来找她,发现她正对着佛像说话,用的是尼泊尔语,可说着说着,就混进了几句藏语,最后竟冒出个中原的词“缘分”。“公主,你在跟佛说什么?”梅朵好奇地问。
尺尊回头笑,眼里的光比酥油灯还亮:“我在说,以后这里的风,既有雪山的凉,也有长安的暖,还有我们家乡的花香。佛听着这些风,才知道我们都好好的。”
这时,殿外传来歌声。是吐蕃的孩童在唱新学的歌谣,歌词里混着尼泊尔的调子和中原的词:“金顶亮堂堂,双佛笑微微,酥油花儿香,汉藏尼是一家……”
尺尊走到殿门口,望着远处的布达拉宫,宫顶的金幢在月光里闪着光。她知道,大昭寺的故事还长着呢,但至少今夜,两尊来自不同地方的佛,在同一盏灯光下,看着同一片土地,听着同一种歌声——就像她和文成公主,和所有在这里的人一样,把不同的根,扎进了同一片土里。
而她额间的“提拉克”印记,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红,像颗跳动的心脏,在两尊佛像的光影里,轻轻搏动着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