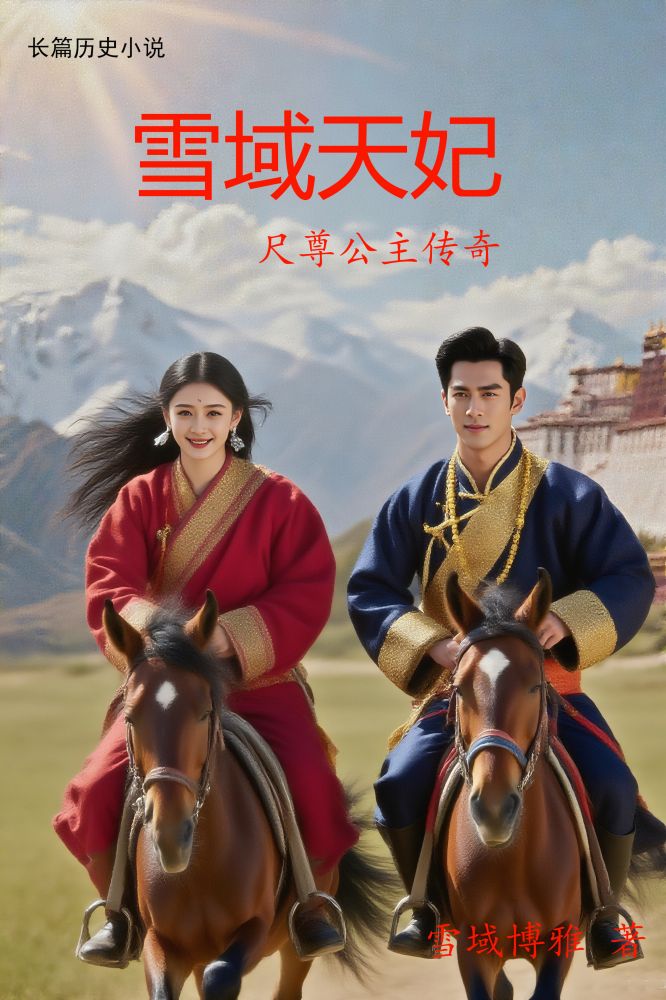
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 第三卷 风的方向第五章 圣像之争的暗流(上)
大昭寺的穹顶在吐蕃的晨光里泛着冷硬的石色,刚砌好的东殿飞檐下,工匠们正用牦牛毛绳将最后一块青石板固定。尺尊公主站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,绛红色的披风被山风掀起一角,露出袖口绣着的尼泊尔金翅鸟纹样。她手中握着一卷桦树皮图纸,指尖在“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供奉台”的标记上轻轻摩挲——这是她亲自绘制的第三版图纸,光是调整佛像底座的高度,就与吐蕃工匠争论了整整七日。
“公主殿下,今日的 mortar(灰泥)按您说的,加了三倍的青稞汁和羊毛。”负责木作的吐蕃匠人顿珠捧着一块晾干的灰泥样本上前,粗糙的手掌在衣襟上反复擦拭,“您看这硬度,就算再过百年,也不会裂。”尺尊公主接过样本,用指甲轻轻划了划,指尖传来坚实的阻力。她微微颔首,目光却越过顿珠的肩膀,落在远处尘土飞扬的山道上。
那是通往逻些城的必经之路,自从上月大唐使团的驿使带着文书抵达后,这条路上的商旅和信使就突然多了起来。昨日她从松赞干布的议事殿回来时,还看到三辆载着大唐丝绸的马车停在小昭寺工地外,车旁的大唐武士腰间佩着的横刀,刀鞘上的缠枝纹在阳光下格外刺眼。
“公主,您在看什么?”侍女巴姆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只看到几个背着盐袋的牧民正牵着耗牛走过,“是不是担心今日的风太大,影响木材晾干?”尺尊公主收回目光,将桦树皮图纸卷好塞进锦袋,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:“不是风,是人心。”
话音刚落,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三匹快马冲破晨雾,为首的骑士翻身下马时,腰间的铜牌“哐当”一声砸在石板上——那是吐蕃赞普直属的“论恐热”(禁军)的令牌。骑士顾不上擦拭脸上的尘土,单膝跪地高声禀报:“公主殿下!赞普紧急召见,大唐使团的副使在议事殿外求见,说有关于佛像供奉的要事需当面商议!”
尺尊公主的心猛地一沉。她早知道大唐不会轻易接受“大昭寺供奉八岁等身像”的安排,却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接地找上门来。她握紧巴姆递来的马鞭,翻身上马时,瞥见东殿墙角处,一个穿着褐色僧袍的僧人正低头整理工具,那僧袍的领口处,隐约露出一块与大唐驿使腰间相同的缠枝纹玉佩。
议事殿内的气氛比殿外的山风还要凛冽。松赞干布坐在鎏金宝座上,左手边是吐蕃大相禄东赞,右手边的空位本该是给尺尊公主的,此刻却站着大唐使团的副使王玄策。这位来自长安的官员穿着深蓝色的朝服,手中捧着一卷明黄色的文书,目光扫过殿内的吐蕃大臣时,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审视。
“赞普陛下,”王玄策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殿内,“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,乃是太宗皇帝亲自甄选的圣物,当年玄奘大师西行归来,曾亲言此像‘集三世佛法之精华’。如今大昭寺作为吐蕃第一座佛法圣地,若将八岁等身像供奉于主殿,恐难彰显大唐与吐蕃的‘甥舅之谊’啊。”
禄东赞立刻上前一步,手中的象牙朝笏在地面上顿了顿:“王副使此言差矣!尺尊公主入藏时,尼泊尔国王将八岁等身像作为国礼相赠,且大昭寺的选址、奠基皆由公主主持,按吐蕃的规矩,先建之寺,当供奉先至之圣像。”
“规矩?”王玄策冷笑一声,展开手中的文书,“据我所知,吐蕃的‘规矩’,也是赞普陛下定的。去年赞普遣使入唐,求娶文成公主时,曾在国书中言‘愿以大唐为尊’,如今不过是一尊佛像的供奉之地,难道赞普陛下要食言?”
这句话像一把尖刀,直插殿内所有人的心脏。松赞干布的手指在宝座扶手上轻轻敲击,目光落在殿外——尺尊公主的绛红色披风正出现在台阶尽头,她的脚步很慢,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所有人的神经上。
尺尊公主走进殿内时,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。她没有先向松赞干布行礼,而是径直走到王玄策面前,目光落在他手中的文书上:“王副使口中的‘甥舅之谊’,难道是靠争夺佛像的供奉之地来维系的?当年文成公主入藏,带去的是大唐的历法与蚕种;我入藏,带去的是尼泊尔的医术与佛经。我们皆为传播佛法而来,若今日因一尊佛像争执,岂不让世人笑话?”
王玄策没想到尺尊公主会如此直接,他愣了一下,随即又扬起下巴:“公主此言有理,但圣像的珍贵程度有别。十二岁等身像是佛陀成道后所造,八岁等身像不过是佛陀少年时的造像,孰轻孰重,一目了然。”
“轻重?”尺尊公主突然提高声音,从锦袋中取出一块晶莹的水晶——那是她从尼泊尔带来的“摩尼宝”,阳光透过水晶,在地面上投射出一道七彩的光痕,“佛陀说众生平等,难道在王副使眼中,连佛陀的造像都分高低?若按年岁论,那刚出生的佛陀像,岂不是要被弃之荒野?”
殿内的吐蕃大臣们纷纷低笑起来,禄东赞更是适时开口:“公主所言极是!佛法讲究‘心诚则灵’,若心中有佛,即便在帐篷里供奉,也是圣地;若心中无佛,就算将佛像供在黄金台上,也无济于事。”
王玄策的脸色涨得通红,他没想到这个来自尼泊尔的公主竟如此善辩,一时竟找不到反驳的话。就在这时,殿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,一个禁军士兵连滚带爬地冲进来,声音带着颤抖:“赞普!不好了!小昭寺工地……工地的佛像底座,被人凿了个大洞!”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松赞干布猛地从宝座上站起来,腰间的佩剑“呛啷”一声出鞘:“怎么回事?!文成公主的十二岁等身像明日就要入寺,底座怎么会被凿?”
士兵趴在地上,声音断断续续:“今早工匠们去开工时,就看到底座中央有个三尺深的洞,洞边还留着……留着一把刻着大唐纹样的凿子!”
王玄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他踉跄着后退一步,指着士兵高声辩解:“不可能!我大唐使团的人昨晚都在驿馆,怎么会去小昭寺?这一定是有人栽赃!”
尺尊公主的目光落在王玄策颤抖的手指上,又转向殿外越来越近的骚动声。她突然想起今早东殿外那个穿着褐色僧袍的人,还有他领口露出的缠枝纹玉佩——那根本不是大唐驿使的配饰,而是去年她在尼泊尔见过的,印度摩揭陀国僧人常戴的样式。
松赞干布的目光在王玄策和尺尊公主之间来回扫视,手中的佩剑在晨光里泛着冷光。殿外的风越来越大,将议事殿的布帘吹得猎猎作响,像是有无数双眼睛,正透过布帘的缝隙,窥视着殿内这场即将爆发的风暴。尺尊公主握紧了手中的摩尼宝,她知道,这场“圣像之争”,从一开始就不是大唐与尼泊尔的较量,而是一场藏在佛法外衣下的阴谋,而那个凿穿小昭寺佛像底座的人,不过是阴谋里抛出的第一颗棋子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