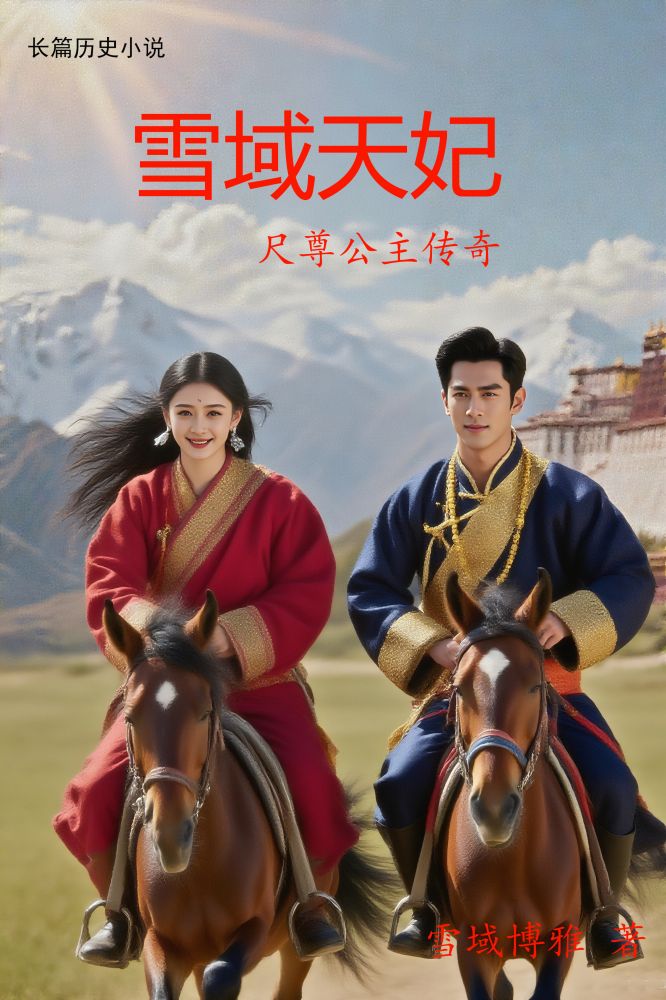
长篇历史小说《雪域天妃:尺尊公主传奇》
第七卷 双脉合流:技艺传承与文明共生
第一章 铜盘秘纹
逻些城的秋阳,像被酥油茶浸润过似的,暖得绵密又醇厚,透过大昭寺金顶的飞檐,在青石板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平措捧着祖父临终前塞给他的青铜盘,指尖反复摩挲着盘沿那圈磨损的纹路——这是平措家族守护了三百年的物件,盘底刻着的“日月同辉”纹样,在阳光下泛着暗哑的光,却没人知道,纹路深处还藏着更隐秘的符号。铜盘的边缘有一处细微的凹痕,是祖父年轻时为护它免受战乱波及,用身体挡住箭矢留下的印记,如今摸起来,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温度。
三日前,大昭寺的堪布亲自登门,绛红色的僧袍上沾着秋露,手里捧着镶金的请柬,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要在近日召集逻些城内的能工巧匠,重启当年尺尊公主带来的“百工技艺册”修订之事。平措作为吐蕃最擅锻铜的家族传人,自然在受邀之列。可他心里清楚,祖父临终前攥着他的手,气息微弱却眼神坚定说出的那句“铜盘见光之日,便是技艺归位之时”,绝非简单的家族嘱托——他幼时曾偷看过祖父深夜对着铜盘喃喃自语,那时祖父总会用松烟在纸上拓印盘底纹路,拓片叠在箱底,足足攒了半箱,只是那些拓片上的符号,他始终看不懂。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爬上大昭寺的红墙,平措便背着铜盘往寺里去。他特意穿上了家族传承的藏青色氆氇长袍,腰间系着嵌银的铜带,带上了祖父留下的青铜小锤——那是当年祖父为大昭寺修缮铜铃时用过的工具,锤身上刻着“平措”二字,是家族世代匠人的印记。沿途的经幡在风里飘展,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五色经幡上的经文被风吹得猎猎作响,转经的老人手里的玛尼轮转得沙沙响,转经筒上的铜饰在阳光下闪着光。偶尔有孩童追着驮着青稞的牦牛跑过,清脆的笑声落在秋草上,惊起几只啄食草籽的麻雀。
平措却没心思看这些熟悉的景致,他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盯着自己,像藏在经幡后的鹰隼,带着探究的意味。他故意放慢脚步,在路过一家卖酥油的小店时,借着整理铜盘背带的动作回头——街角转经筒旁,一个穿着尼泊尔商人服饰的男子正低头整理货囊,男子的藏青色头巾边缘绣着帕坦古城特有的莲花纹样,手里的货囊用牛皮绳捆得紧实,露出一角泛黄的羊皮卷。那男子似是察觉到他的目光,突然抬起头,两人的目光撞了个正着——男子的眼眸是深棕色的,像尼泊尔山谷里的湖泊,带着一丝慌乱,又飞快地移开,指尖却悄悄攥紧了藏在袖中的羊皮卷,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进了大昭寺的偏殿,松赞干布已坐在紫檀木椅上,椅背上铺着整张的豹皮,彰显着赞普的威严。他身旁站着几位大臣,左边是吐蕃的大相禄东赞,手里捧着写满议事的木简;右边是负责邦交的大臣尚论,腰间挂着尺尊公主当年带来的尼泊尔玉佩。还有一位穿着汉地服饰的老者,鬓角染霜,手里捧着一卷泛黄的竹简,竹简用红绳系着,绳结是汉地特有的“吉祥结”,正是从长安请来的史官李墨——李墨曾随唐使入吐蕃,因精通梵文与吐蕃文,被松赞干布留下整理史料。
平措刚要屈膝行礼,松赞干布便摆了摆手,声音沉厚如雪山融水,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:“平措,不必多礼。今日请你来,是想让你看看这册‘百工技艺册’——当年尺尊公主从尼泊尔带来的技艺,如今纺织的‘云锦法’、建筑的‘斗拱术’都已渐渐失传,赞蒙赤尊公主特意嘱咐,要让吐蕃的匠人重拾这些技艺,让两国的手艺能一代代传下去。你是锻铜世家,或许能从册子里寻到些线索。”
李墨上前一步,将竹简轻轻放在案几上,竹简的边缘已有些磨损,显然是被反复翻阅过。他小心翼翼地展开,生怕损坏了这珍贵的史料:“这册技艺册是当年尺尊公主亲自修订的,用吐蕃文与梵文对照书写,每一页都盖着公主的‘雪域天妃’印鉴。你看这锻铜部分,记载得尤为详细。”
平措凑近案几,目光落在锻铜章节的文字上——“以雪山铜为料,需取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铜,经冰水浸泡三日去杂质;掺三钱金沙,需是尼泊尔河谷出产的‘日光沙’,色泽如金;经七七四十九日锻造,每日锻打需在辰时到午时之间,借日光之力;可成‘日月盘’,盘纹能映出山川脉络,遇经幡影子则显秘纹”。
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平措心头炸开——祖父留下的青铜盘,不正是“日月盘”吗?他记得小时候,祖父曾在正午时分将铜盘放在经幡下,那时盘底的纹路确实隐约有光影流动,只是当时他年纪小,以为是阳光的错觉。他急忙从背上取下铜盘,铜盘被棉布包裹着,解开棉布时,还能闻到淡淡的酥油香气——那是家族世代用酥油保养铜器的习惯。他将铜盘轻轻放在案几上,铜盘与竹简上的文字相对,仿佛跨越千年的呼应。
“赞普,小人家里有一物,或许与这技艺册有关。”平措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,指尖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。
铜盘刚放在案上,偏殿的门突然被风吹开,门外的经幡被风吹得飘进殿内,影子恰好落在盘底。原本模糊的“日月同辉”纹样竟渐渐清晰起来,纹路间浮现出几行细小的梵文,像是用金线绣在铜盘上似的。李墨急忙凑上前,从袖中取出放大镜(那是他从长安带来的汉地器物),仔细辨认着梵文:“这是尺尊公主的笔迹!我曾见过公主写给唐王的书信,笔迹与此一模一样。上面写着‘日月盘为引,百工为脉,待雪域花开,技艺归藏’——‘雪域花开’,或许就是指今日这样,技艺册与铜盘相遇的时刻!”
松赞干布站起身,高大的身影笼罩在铜盘上方,他伸出手指,轻轻拂过铜盘上的梵文,指尖能感受到纹路的凹凸,目光变得深邃:“看来,尺尊公主当年留下的不只是技艺册,还有这铜盘作为钥匙。平措,你可知这铜盘还有什么秘密?比如你祖父是否曾留下过关于秘纹的记载?”
平措摇了摇头,正要开口说祖父从未提过更多细节,殿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,伴随着侍卫的呵斥声。紧接着,两个侍卫押着一个男子走进殿内,正是平措在街角看到的那位尼泊尔商人。男子怀里的羊皮卷掉在地上,侍卫刚要去捡,松赞干布摆了摆手:“让他自己捡起来。”
男子跪在地上,颤抖着捡起羊皮卷,羊皮卷展开后,上面画着与铜盘相同的“日月同辉”纹样,只是在纹样的右下角,多了一个红色的标记——那是一朵莲花,花瓣上刻着细小的梵文。标记旁用吐蕃文写着“尼泊尔帕坦古城,铜匠世家莉娜家族”。
商人见事情败露,额头渗出冷汗,急忙磕头求饶:“赞普饶命!小人并非有意冒犯,只是身负家族使命,不得不来逻些寻找‘日月盘’。小人是尼泊尔莉娜家族的传人,名叫阿吉,家族世代守护着尺尊公主留下的锻铜图谱,此次来逻些,是为了完成祖父的遗愿——找到‘日月盘’,复原公主当年的锻铜技艺。”
松赞干布让侍卫扶起阿吉,语气缓和了些:“莉娜家族?我曾听尺尊公主提起过,说你们家族是尼泊尔最擅锻铜的家族,当年公主为大昭寺铸造释迦牟尼佛像时,莉娜家族的先祖曾来帮忙。阿吉,你说说,这铜盘与莉娜家族的图谱,到底有什么关联?”
阿吉站起身,拍了拍身上的灰尘,双手捧着羊皮卷,走到案几前,指着红色莲花标记说:“图谱上记载,尺尊公主离开尼泊尔前,担心锻铜技艺在战乱中失传,便将核心技艺分成两部分。一部分藏在逻些的‘日月盘’里,记录的是‘锻铜之魂’,也就是火候、材料的选择;另一部分留在帕坦古城的莉娜家族,是‘锻铜之形’,也就是佛像、器物的模具图谱。只有两部分合在一起,才能复原最完整的锻铜技艺,尤其是‘金身佛像锻造法’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大昭寺的方向,带着一丝惋惜:“当年公主为大昭寺铸造的释迦牟尼佛像,便是用这种方法锻造的,佛像的金身能映出日光,无论过多少年都不会黯淡。可后来因为吐蕃与尼泊尔的战乱,技艺渐渐失传,佛像的金身也因为没有正确的保养方法,慢慢失去了光泽。我祖父临终前说,只有找到‘日月盘’,才能让佛像重现金身,让两国的锻铜技艺重新联结。”
平措这才明白,祖父守护铜盘,不仅是家族使命,更是为了等待莉娜家族的传人。他看着阿吉手里的羊皮卷,又看了看案上的铜盘,突然想起小时候祖父教他锻铜时说的话:“铜是有灵性的,你对它用心,它便会为你显露出最真的模样。两国的技艺也是一样,只有心连在一起,才能让手艺传得远。”
他伸手拿起铜盘,又示意阿吉展开羊皮卷,将两者放在一起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——铜盘上的秘纹与羊皮卷上的图谱竟完美地拼合在一起,形成了一幅完整的锻铜流程图:从雪山铜的开采,到金沙的筛选,再到锻打的步骤、模具的雕刻,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。图谱的中央,画着一尊金身佛像,佛像的底座上,刻着“中尼同源,技艺共守”八个梵文大字,字体苍劲有力,正是尺尊公主的笔迹。
松赞干布看着拼合的图谱,眼中露出赞叹之色,他转身对在场的大臣说:“尺尊公主当年的用心,原来是为了让中尼两国的匠人世代相守,共同传承技艺。这不仅是手艺的传承,更是两国友谊的传承。”他又看向平措与阿吉,语气郑重:“平措,阿吉,你们二人既是两国锻铜世家的传人,便担起这个使命吧——明日起,你们在大昭寺开设工坊,召集两国的能工巧匠,一起复原‘金身佛像锻造法’。我会让大昭寺提供最好的场地,让国库拨付所需的材料,务必让尺尊公主的技艺,重新在雪域绽放光芒。”
平措与阿吉对视一眼,眼中都充满了激动与坚定。他们同时跪地领命,额头触碰到冰凉的青石板,却感受到了沉甸甸的使命。夕阳西下时,他们走出大昭寺,秋风吹动着两人的衣角,远处的雪山在暮色中泛着银光,像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巨人。平措握着铜盘,阿吉揣着羊皮卷,两人并肩走在青石板路上,脚步声与转经筒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,像是在谱写一首跨越千年的友谊之歌。
接下来的几日,平措与阿吉在大昭寺旁的空地上搭建了临时工坊。工坊的选址是平措选的——这里正对着大昭寺的金顶,每日能最先感受到日光,符合“借日光锻造”的要求。消息传开后,逻些城内的吐蕃匠人纷纷赶来,有擅长锻铜的、有精通雕刻的、有懂得熔炼的;从尼泊尔来的手工艺人也闻讯而来,他们大多是莉娜家族的旁支,带着自家的工具和祖传的技艺;甚至还有几位从汉地来的工匠,是随唐使留在吐蕃的,擅长木工、漆艺,也主动提出帮忙。
工坊里,炉火日夜不熄,黑色的烟囱里冒出的烟在秋空中散开,与大昭寺的香火烟交织在一起。铜锤敲打铜坯的声音“叮叮当当”,与工匠们的交谈声、笑声交织在一起。吐蕃语、尼泊尔语、汉话不时响起,却丝毫不妨碍彼此的沟通——一个手势、一个眼神,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,因为对技艺的热爱,早已超越了语言的隔阂。
平措负责熔炼雪山铜,他按照图谱上的记载,将从雪山运来的雪铜块敲碎,每一块都要敲成拳头大小,再放入冰水浸泡。冰水是从大昭寺的水井里打来的,井水里含有雪山融水,符合“去杂质”的要求。浸泡三日期间,他每日都要更换一次冰水,还要用木勺搅动铜块,确保每一块铜都能充分接触冰水。“雪铜性烈,只有用冰水浸泡,才能让它变得温顺,锻打时不易开裂,”他一边教旁边的年轻吐蕃匠人丹增,一边回忆祖父当年的教导,“祖父说,锻铜就像做人,急不得,要慢慢熬,要学会用耐心去驯服材料,而不是用蛮力。”
丹增是逻些城里年轻匠人中的佼佼者,却总有些急于求成。听了平措的话,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:“平措师傅,我以前总觉得锻打得越用力越好,现在才知道,原来火候和耐心比力气更重要。”
阿吉则负责绘制佛像的模具,他带来了莉娜家族祖传的羊皮纸,这种羊皮纸用尼泊尔特有的植物汁液浸泡过,防水防潮,能保存百年。他先用炭笔在羊皮纸上画出佛像的轮廓,每一笔都要反复修改——佛像的身高要三尺六寸,象征“三十六天”;佛像的衣纹要流畅,像流水一样自然;佛像的手势要做“施愿印”,指尖的弧度要恰到好处,既显庄重又显慈悲。
“这是尺尊公主当年定下的规矩,”阿吉一边用细竹条调整轮廓,一边向周围的匠人解释,“公主说,佛像不仅是信仰的象征,更是技艺的结晶。每一笔每一划,都要带着敬畏之心,因为你手中的工具,不仅在雕刻木头,更是在雕刻人心——看到佛像的人,能从衣纹里感受到温暖,从眼神里感受到希望,这才是最好的技艺。”
旁边一位尼泊尔老匠人接过话茬:“阿吉少爷说得对,我小时候听祖父说,当年莉娜家族的先祖为了雕刻佛像的眼睛,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,每天只刻一笔,就是为了让佛像的眼神更传神。”
工坊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,有位汉地来的木匠,名叫张木,擅长汉地的榫卯工艺。他见平措和阿吉打造佛像底座需要雕花,便主动提出帮忙:“我从长安来逻些时,就听说尺尊公主带来了很多技艺,如今能参与其中,是我的荣幸。汉地的榫卯工艺不用一根钉子,能让底座更稳固,我还能在底座上雕刻‘缠枝莲’纹样,与尼泊尔的莲花标记呼应,象征两国技艺的交融。”
张木说着,便拿出工具开始测量底座的尺寸,他的工具包是用汉地的帆布做的,里面整齐地放着刨子、凿子、刻刀,每一件工具上都刻着他的名字。“你们看,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刻刀,当年他为长安的大慈恩寺雕刻过佛像底座,”张木拿起一把小巧的刻刀,刀刃闪着寒光,“今日用它来雕刻中尼合璧的佛像底座,也算是完成了父亲的心愿。”
日子一天天过去,雪山铜在冰水中浸泡够了三日,取出时,铜块的表面泛着淡淡的银光,杂质都已沉淀在水底;佛像的模具也雕刻完成,羊皮纸上的佛像轮廓清晰,细节精美,阿吉还在佛像的衣纹里加入了吐蕃的“祥云纹”和尼泊尔的“莲花纹”,让佛像既有雪域的庄重,又有尼泊尔的灵动。
接下来便是铸造佛像的关键步骤——将熔炼好的铜水倒入模具。铸造那天,大昭寺的堪布亲自来主持仪式,他手持经筒,念诵着《金刚经》的经文,声音洪亮而庄严。工匠们穿着整洁的衣服,按照仪式的要求,排成两列站在模具旁,平措与阿吉站在最前面,手里捧着装满青稞酒的木碗——这是吐蕃的传统,铸造前要敬天地、敬祖先、敬技艺。
“敬尺尊公主,愿技艺传承不息!”平措举起木碗,声音坚定。
“敬中尼匠人,愿友谊世代相传!”阿吉也举起木碗,眼中满是虔诚。
工匠们纷纷举起木碗,将青稞酒一饮而尽,酒液顺着嘴角流下,带着淡淡的醇香。随后,平措与阿吉走到熔炉旁,
熔炉里的火焰早已烧得旺盛,是阿吉按照莉娜家族的“圣火炉”技法点燃的——用晒干的高山杜鹃木作引,掺入少量尼泊尔特有的“檀香松”,火焰呈淡蓝色,温度比普通炉火高出三成。平措戴着祖父留下的铜制护目镜,手里握着长柄铜勺,铜勺的柄上缠着隔热的羊毛布,他小心地将浸泡好的雪山铜块与金沙按比例投入熔炉,铜块接触火焰的瞬间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,金色的火星从炉口溅出,落在地上,像散落的星辰。
“火候要稳,不能急,”平措一边搅动炉中的铜料,一边对身旁帮忙的丹增说,“图谱上写着,熔炼时要保持‘文火慢烧’,辰时到午时之间,每隔一个时辰要添一次檀香松,让火焰始终保持淡蓝色。如果火焰变成红色,说明温度太高,铜料会变脆;如果变成黄色,温度不够,铜料融不透,铸造出来的佛像会有裂痕。”
丹增认真地记着,手里拿着松烟笔,在木简上记录下平措说的每一个要点:“辰时添檀香松,午时查铜水颜色,铜水呈淡金色为最佳。”他的字迹虽然有些稚嫩,却写得格外认真,木简的边缘,还画了一个小小的火焰图案,用来标记火候的颜色。
阿吉则在一旁检查模具的密封性,他用尼泊尔的“树胶”涂抹在模具的缝隙处,这种树胶是从帕坦古城的榕树上采集的,晒干后黏性极强,能防止铜水渗漏。“模具的密封性很重要,”阿吉一边涂抹树胶,一边对张木说,“当年莉娜家族的先祖曾因为模具缝隙没封好,导致铜水渗漏,浪费了整整一炉的铜料,后来先祖用了三天时间,重新采集树胶,才将模具封好。从那以后,莉娜家族就定下规矩,铸造前要反复检查模具,确保没有一丝缝隙。”
张木点点头,拿起一块小木板,轻轻敲打模具的外壳,听着声音判断模具是否牢固:“汉地有句话叫‘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’,模具就像工匠的‘器’,只有把‘器’做好了,才能铸造出好的佛像。”
午时刚到,平措用长勺舀起一点铜水,铜水在勺中泛着淡金色的光泽,像融化的阳光,滴落在冷水中时,发出“嗤”的一声,凝固成一小块铜块,表面光滑,没有任何气泡。“火候到了!”平措兴奋地喊道,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。
工匠们立刻按照分工行动起来:丹增和几位年轻匠人抬着熔炉的支架,将熔炉慢慢移到模具上方;张木和几位木匠守在模具旁,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;阿吉则拿着一把小铜锤,站在平措身边,准备在铜水倒入时,轻轻敲打模具,让铜水更好地填满模具的每个角落。
平措深吸一口气,双手握住长柄铜勺,将铜水缓缓倒入模具的入口。铜水流动时,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,像雪山融水流入江河,蒸汽从模具中升腾而起,带着铜的金属气息和檀香松的香气,在阳光下形成一道淡淡的彩虹。阿吉按照图谱上的要求,每倒入一勺铜水,就用小铜锤轻轻敲打模具的侧面,“笃笃笃”的敲击声,与铜水流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像是在为佛像的诞生伴奏。
铜水一点点填满模具,平措的额头上渗出了汗水,汗水顺着脸颊流下,滴落在地上,他却顾不上擦——他的目光紧紧盯着模具的入口,看着铜水的液面慢慢上升,生怕出现一丝差错。阿吉看出了他的紧张,轻声说:“别紧张,平措兄弟,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,尺尊公主会保佑我们的。”
平措点点头,想起祖父当年铸造铜铃时的场景——那时祖父也是这样,专注地盯着熔炉,汗水浸湿了衣衫,却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手势。他握紧手中的铜勺,继续倒入铜水,直到模具被铜水完全填满,入口处的铜水微微凸起,像一颗饱满的铜珠。
“好了!”平措放下铜勺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。工匠们也都露出了笑容,张木擦了擦额头的汗,说:“这是我来吐蕃后,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,比在长安雕刻佛像还要开心。”
接下来便是等待铜水冷却,按照图谱上的记载,需要等待三天三夜,期间不能移动模具,也不能让模具受到风吹雨淋。工匠们轮流守在工坊里,白天用羊毛毯盖住模具,防止阳光直射;晚上则在模具旁点燃酥油灯,保持周围的温度稳定。平措和阿吉几乎没有离开过工坊,他们每天都会来到模具旁,用手触摸模具的外壳,感受里面铜水的冷却情况,偶尔还会低声交谈,想象着佛像铸造成功后的模样。
第三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平措和阿吉便早早地来到工坊,准备拆开模具。工匠们也都陆续赶来,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神情。大昭寺的堪布也来了,手里捧着一串佛珠,为佛像的“出世”祈福。
平措拿起祖父留下的青铜小锤,轻轻敲向模具的外壳。“笃”的一声,模具的外壳出现了一道裂缝,阿吉立刻用手扶住模具,防止外壳碎裂时损伤里面的佛像。平措继续敲击,裂缝越来越大,木屑从裂缝中掉落,露出里面泛着金光的佛像边缘。
“小心点,慢慢来,”阿吉提醒道,声音有些颤抖。
平措点点头,放慢了敲击的速度,每一次敲击都恰到好处,既不会损伤佛像,又能让模具外壳顺利脱落。随着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模具的外壳完全拆开,一尊半人高的金身佛像赫然出现在眼前——佛像的金身泛着柔和的光芒,像被日光浸润过似的,在清晨的微光中,每一寸铜面都闪着细腻的光泽;佛像的衣纹流畅自然,“祥云纹”与“莲花纹”交织在一起,在衣摆处形成一个完美的弧形;佛像的手势是“施愿印”,指尖的弧度恰到好处,仿佛正准备为世人拂去烦恼;佛像的眼神慈悲安详,眼珠是用尼泊尔的黑曜石镶嵌的,在光线下,像蕴含着一汪深潭,让人看一眼便心生安宁。
底座上的“中尼同源,技艺共守”八个梵文大字,在阳光下格外清晰,字体的边缘经过精心打磨,摸起来光滑而温润。工匠们都忍不住围上前,发出阵阵赞叹,丹增伸手轻轻触摸佛像的衣纹,惊讶地说:“这衣纹就像真的丝绸一样柔软,一点都不像铜铸的!”张木则盯着底座的榫卯结构,满意地笑了:“你看这榫卯,严丝合缝,不用一根钉子,能让佛像稳稳地站在这里,就算再过百年,也不会松动。”
没过多久,松赞干布与赤尊公主也亲自来到工坊。松赞干布走到佛像前,仔细端详着佛像的每一个细节,眼中露出赞叹之色:“这才是尺尊公主想要留下的技艺,是两国匠人用心浇灌出的成果。你们不仅复原了锻铜技艺,更让中尼两国的友谊,在这尊佛像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。”
赤尊公主走到佛像旁,轻轻抚摸着佛像的金身,她的指尖划过佛像衣纹中的“莲花纹”,眼中满是温柔:“当年尺尊公主来吐蕃,不仅带来了佛教,更带来了两国的友谊与技艺。她曾对我说,技艺是没有国界的,就像阳光能照耀到每一片土地,好的技艺也能连接每一颗心。如今,这份友谊与技艺,终于在我们手中延续下去了。”
赤尊公主转头看向平措与阿吉,语气郑重:“平措,阿吉,你们做得很好。从今日起,平措家族与莉娜家族,便是吐蕃与尼泊尔的‘技艺使者’。我会下令,在大昭寺旁修建一座‘双脉工坊’,让你们能在这里继续传授锻铜技艺,让更多的匠人学会‘金身佛像锻造法’,让尺尊公主的精神,永远流传下去。”
平措与阿吉再次跪地谢恩,起身时,两人的目光里都充满了坚定。阳光透过工坊的窗户,照在佛像的金身上,反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,落在工匠们的脸上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当天下午,大昭寺举行了盛大的佛像安放仪式。百姓们闻讯赶来,沿着青石板路排成两列,手里捧着酥油、青稞,为佛像祈福。平措与阿吉亲自抬着佛像,一步步走向大昭寺的偏殿,工匠们跟在后面,敲打着铜铃、吹奏着法号,声音响彻逻些城的上空。
佛像被安放在偏殿的正中,堪布为佛像举行了开光仪式,当酥油灯的光芒照亮佛像的脸庞时,百姓们纷纷跪地朝拜,口中念着“尺尊公主保佑”。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拄着拐杖走到佛像前,老泪纵横:“我小时候见过大昭寺的金身佛像,后来佛像的金身黯淡了,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那样的光芒了。没想到今天,我又看到了,就像尺尊公主当年带来的光芒,又回到了逻些城。”
平措站在佛像旁,指尖再次摩挲起那枚青铜盘,盘底的纹路在酥油灯的光芒下显得格外清晰。他知道,这枚铜盘的故事,才刚刚开始——它不仅连接了中尼两国的技艺,更连接了两国百姓的心。而这份连接,会像雪山一样坚定,像江河一样绵长,在雪域高原上,永远流淌下去。
夜幕降临时,逻些城的百姓还在大昭寺外载歌载舞,庆祝佛像的诞生。平措与阿吉坐在工坊的门槛上,看着远处热闹的人群,手里捧着温热的酥油茶。“平措兄弟,”阿吉喝了一口酥油茶,笑着说,“等‘双脉工坊’建好,我们就把两国的匠人都请来,一起研究更多的技艺,不仅是锻铜,还有纺织、建筑,让尺尊公主留下的所有技艺,都能重新绽放光芒。”
平措点点头,目光望向尼泊尔的方向,那里的夜空与逻些城的夜空一样,缀满了星星:“好,我们还要把这里的故事告诉莉娜家族的人,告诉吐蕃的百姓,让所有人都知道,中尼两国的友谊,是用技艺和真心浇灌出来的,永远不会褪色。”
夜风吹过工坊,带来了经幡的香气和百姓的歌声,青铜盘静静地躺在平措的膝上,盘底的“日月同辉”纹样,在星光下泛着柔和的光,像是在见证着这跨越千年的友谊新篇章。
















